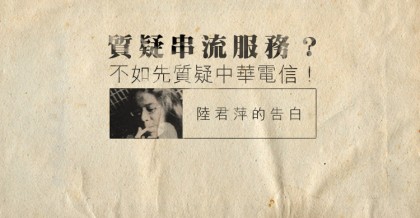從小學習打擊樂的蘇郁涵,因為喜歡爵士樂而接觸鐵琴,演奏這樂器時領會到自由,貼近於她不順應傳統的性格。台北藝術大學管弦與擊樂研究所一畢業,她即遠赴美國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主修爵士鐵琴演奏。
為求爵士離家園,不像大多數的本土爵士樂手,完成學業即返台發展,蘇郁涵選擇沉浸在紐約爵士音樂圈。這 10 年間,她陸續推出《孤獨飛行》、《自己的房間》及《城市型動物》等專輯,不僅獲得金曲/金音獎肯定,作品更曾被美國爵士樂最重要雜誌《DownBeat》評價為「像是一本最好的小說,說盡了所有的美好」與 All About Jazz 網站的「年度最佳專輯」。
-1024x684.jpg)
沈潛 5 年後,蘇郁涵新專輯《自由的姿態》,囊括了紐約前衛爵士界一流頂尖好手,探索即興演奏在精密繁複的架構下,如何衝撞出無限的自由,並同時享受著色彩滿溢的情感流動。
身為女性爵士樂手,蘇郁涵並沒有特別迷戀或過分談論女性主義,但認為「女生詮釋音樂的方式,再怎麼說還是很不一樣」,尤其是吹奏管樂器,發出來的聲音質地明顯不同。無論標題是獻給作家 Joan Didion 的〈Didion〉,或是結合文字與詩的〈She Goes to a Silent War〉,她在新專輯《自由的姿態》有寫到一些女性議題,於是找了薩克斯風手 Caroline Davis 加入,在聲音的表現上,與以往專輯有很大的不同。
此篇專訪由謝明諺向蘇郁涵提問,延續【吹專訪】在音樂上,真正的自由應該是這個樣子:謝明諺和好友林華勁談他的新專輯《Our Waning Love》的音樂人對談模式。站在浪尖上的兩位爵士樂手,不但演奏過且熟悉彼此的作品,近期不約而同都發表了新作,打開自己的樂器持續發出刺激性的聲音。
他們透過視訊螢幕,以《自由的姿態》起頭,討論女性樂手詮釋音樂的方式、前衛爵士樂場景、爵士樂的專輯錄音標準,以及冰島歌手 Laufey 走紅引發的現象。

與前衛爵士樂手共冶一爐
謝明諺(以下簡稱「謝」):我覺得跟上一張專輯有很像的地方,也有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鋼琴,和聲的樂器回來;另外一面,薩克斯風手換了、鼓手也換了,改變很多,音樂 play 的方式、聲音的配置也不太一樣。
蘇郁涵(以下簡稱「蘇」):上張專輯《城市型動物》大致做的是一個靠近 Modern Jazz 與 Post-Bop 的作品,融入我喜愛的情境式作曲手法。專輯發完,我覺得自己在那個風格已經走到一個頂點了,不知道要去哪裡了。我一直都很喜歡更前衛一點的音樂人,決定就放手往這方面更深入的去探索。因此新專輯《自由的姿態》(Liberated Gesture)中加入的鋼琴手 Matt Mitchell、鼓手 Dan Weiss 都是在前衛爵士界風格獨具的領頭人物。
紐約有一種類型的前衛爵士,結構是非常精密的,它融入了現代樂。也許有各種變化的拍號,或是比傳統爵士樂更複雜的和聲,運用更廣一點的即興方式。這方面的音樂一直很吸引我,但早些年我一直想著還是先把爵士樂練好吧?這個等到後面一點再做,而這次開始要做新的東西,我覺得我準備好了,「就往這個方向去吧!」
-1024x683.jpg)
謝:相同的部分,這些作曲還是很像妳:譬如說以前「夸父三部曲」、「說再見的三種情境」或是〈Freezing Point〉。因為我也有演過,可以感覺出來妳的個性,或是對旋律的 arrange 的方式,節奏與旋律去互相 against,很多這樣子的段落。
但就像妳剛講的,Dan Weiss 是很 percussive 的,他跟之前「很爵士」的鼓手很不一樣。你看像他打〈Hi-Tech Pros and Cons〉或〈Siren Days〉,有些地方是超級簡單的四四拍,在底下鋪一個超級清楚的東西,清楚到會整個跳出來。但是上面的薩克斯風、鋼琴或是鐵琴的 pattern,節奏比較複雜一點,against each other 這樣子。
蘇:跟 Dan Weiss 的合作是很有趣的體驗,很多樂迷對他的印象是,擅長於各種非常變態的拍子。平常跟他一起演 standard,他會給你打一些完全出乎意料不是四四拍的東西,然後聽到其它樂器都在做一些很複雜的事情的時候,突然就來了個四四。
-1024x683.jpg)
謝:是有一派的鼓手很喜歡做這樣的事情。不是故意要挑戰,或是刻意的去 lead 音樂的方向,但是可以給的很巧。例如在很難的東西裡面,鋪一個很簡單的底,其實也是編曲空間的考量。真的非常非常高明的音樂家,他才會去做這些事情。
蘇:等於說,我知道會很多可能性,知道他會隨時出招,把你丟進一個 wilder pool,讓這個音樂一直都有更多的選擇;而身為接招的人,膽子就得更大,或說自己要更穩吧!
謝:另外薩克斯風手 Caroline Davis 其實也滿有趣的,她跟 Alex LoRe 很不一樣。妳第一次傳新專輯檔案給我聽的時候,我以為 Alex 怎麼個性、approach 改變這麼多?聲音有些部分還滿像的,即興的方法不一樣。Caroline 柔軟很多,她給出來的元素,更貼著每首曲子在走、更在當下。怎麼說?有些爵士樂手,尤其是薩克斯風手,因為練習很多東西,我們就會想要講很多事情,或是要用很多東西進去。
-1024x817.jpg)
女樂手的 blood
蘇:新專輯會找 Caroline Davis 的原因之一是——這張專輯有寫到一些女性議題。即便,我沒有很迷戀、過分談論女性主義這方面的事情,但女生詮釋音樂的方式,再怎麼說還是很不一樣。如果是吹管樂器,身體發出來的聲音質地,尤其很不一樣,我想要在新專輯《自由的姿態》多一點這種女性的元素。
謝:另外,很有趣的就是,現在這個節奏組,可能因為 Dan Weiss 的關係,變得非常的 percussive ,再加上妳是鐵琴,所以整個又更 percussive ,這對比很有趣,在之前的專輯比較沒有,之前感覺大家都是同一路。可是新專輯《自由的姿態》有一個更打開的樣子。
蘇:我也算是 Caroline Davis 的 fan,一直都非常喜歡她的各種專輯,風格非常多元,有爵士的,也有融入很多電子的,也有 Indie Rock 的專輯。她對音樂的詮釋非常全面。最近跟她演出的時候,特別感覺到像你剛剛提到的,她很在那個當下,真的深入音樂把它推到更遠的地方。
對啊!這不是每個樂手都會做到,很多人可能 solo 就是想像兩三個 chorus。可是她在演奏的時候,不會讓你覺得她會想著那樣的限制,她會在當下把音樂一直往前去推進。
謝:還有一點:因為鋼琴回來了有更多⋯⋯很塊狀的聲響表現,也讓我想起第 2 張專輯《自己的房間》那時期的作品,或是首張專輯《孤獨飛行》會有一些漂亮的和聲。而在上一張專輯《城市型動物》裡則有一些 polyrhythm 的東西 against 在一起。這次新專輯《自由的姿態》有一點把剛剛提到的元素都結合。
蘇:鋼琴也是一個關鍵。過往專輯都沒有認真的用到鋼琴手,新專輯就特別想要加入,更多東西就可以玩。加上 Matt Mitchell 是我非常喜歡的鋼琴手,也真的讓我學習到很多。

譬如說,新專輯的〈Liberated Gesture IV. Hartung’s Light〉就是很正常的 Modern Jazz 的曲子,很多小 twist,但就和聲或是節奏,並不是說真的很複雜,這種平常彈一些超瘋狂東西的人,彈起那樣的東西,還是有漂亮的觸鍵和優雅 lyrical 的表現,每次聽那首還是超級感動。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夠到達這樣的境界。
謝:他們成長過程一定早就練過了 Herbie Hancock、Chick Corea、Brad Mehldau、McCoy Tyner、Bill Evans 這些。如果從爵士樂的派別或風格來看,哪一個時期對妳影響比較大?
蘇:我做的東西都是很綜合的影響,很多人也許都會這樣吧?我還是一直很喜歡 Miles Davis Second Quintet 的後期作品。我寫新專輯的前期在巴黎,那時候很常聽《Bitches Brew》。Miles Davis 從一個風格慢慢的轉變,變得越來越 open,但還是帶有傳統爵士的東西。我自己也一直很想要把那一塊保存在我的音樂裡面。
另外,我近年一直都很迷紐約的爵士廠牌 Pi Recordings,我最喜歡的一位是薩克斯風手 Steve Lehman。他有非常多超棒的作品,運用微分音、繁複的節奏,或是結合了電子和饒舌的東西。整體來說,我應該是這兩者的融合吧?
謝:感覺的出來,其實妳大部分的作品,其實都還是給人這種⋯⋯有點 on the edge,好像有點危險。我們在 play 的時候,也會覺得有時不小心會「掉出去」。妳有聽很多 M-Base 的東西?但是妳的音樂跟 M-Base 很大的不同是——他們大部分的作品都非常的 masculin,man 到一個不可思議。
但是女性音樂家不是這個樣子⋯⋯也不是女性音樂家不會。我在女性音樂家裡面不會聽到這麼硬⋯⋯也不能講兇猛,可是 M-Base 就是非常的 man,好比一堆肌肉男在秀自己的節奏可以多難多屌,可能拍號什麼都不一樣,但是我們可以順著過去。
蘇:我也喜歡 M-Base、Steve Coleman 很多的東西,喜歡那樣的聲響,可是沒有真的很迷超級精確算數的那種。
謝:妳提到的《Bitches Brew》,Miles Davis 在早期剛開始進到 Fusion 的時候,他還是保留了就是以前 Second Quintet 的那種 free、open。但是到《On the Corner》可能和弦、和聲樂器是非常自由的,底下卻有複雜的節奏在前進。
蘇:關於當代女性樂手,我特別喜歡的還有吉他手 Mary Halvorson,和薩克斯風手 Anna Webber。他們的音樂都有很 structure 的部分,也有某種女性的 blood 在。那些是我天生擁有,並且喜歡的東西,所以很自然的去做它。
該堅持還是要 follow?
謝:其實就是很妳的東西。因為很熟悉妳的 play,這些曲子也都演奏過。可能從 2011 年到現在,整個演進的過程都有參與到。非常恭喜,我覺得新專輯《自由的姿態》做的非常非常好!
蘇:當然一直都是想要做自己的東西,可是在職業的路上,很容易被很多東西影響及被牽制,你會覺得說:「喔!我是不是應該要做像這樣一點啊?或像那樣一點啊?」這些想法都會在創作過程,閃過你的腦海。
我一開始寫這張專輯的時候,因為在巴黎駐村,滿特別的一個經驗。在那裡有個工作室,什麼都不用擔心,其實有一點覺得 anyway what the fuck,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完全不要去管說:「喔!這個東西有沒有主流啊?有沒有幹嘛啊?有沒有很爵士啊?」開頭是有這樣的念頭。
謝:至少在寫作品,或是給的標題,還是很妳現在的狀態。再加上妳用的樂手,其實都還是非常當代的這些,play 的方法、involving 的音樂都在現在的時間點上,聽起來就是 2010 年代、2020 年代的爵士樂。不是那種⋯⋯要回歸吹 Bebop 或是要很 Lennie Tristano 的風格。
蘇:理想是可以做這樣的東西。我覺得跟處在的地方有關,已經在紐約這麼多年了,你會被很多同儕的影響,大家都還是想盡辦法,衝在這個音樂的前端,你會聽到很多很新、很好玩的東西。但我總覺得現在的爵士樂圈,反而變得有點復古?可能是遇到社交媒體各種影響。
謝:社交媒體上面大部分的閱聽者,可能都是學生,沒有這麼直接了解當代的爵士樂場景。
Pat Metheny 之前也有說過,他們年輕的時候,音樂做出來是給同輩們聽的。可是到了他們的下一輩的時候,突然出現一群人,音樂是要演給他們上一代的人聽。他在講的就是那些 Young Lions,開始回來復古,要吹 Bebop 要穿西裝要 acoustic 那樣子。社交媒體造成滿多影響,所以妳看現在真的超級紅的樂手,其實是就是網紅。他們就是吹非常老、非常傳統的,寫下來很清楚的東西,可以練 12 個調的東西。
蘇:所以我覺得滿妙的,走到那麼現代之後,突然好像很復古。剛剛你講到場景,我剛好前兩天也看了 YouTuber 在討論 Laufey 走紅的現象、討論這是不是爵士樂。也是滿有趣的議題,他也提到說,這樣是很不錯的,吸引很多新世代的人喜歡爵士樂。可是 Laufey 沒有真的 involved 在真正爵士樂的場景⋯⋯
謝:她自己也說,她不算爵士樂。
蘇:造成那些年輕的群眾,也沒有在那些場景認識到爵士樂。
謝:嗯,但我覺得滿有趣的。我有看 Adam Neely 那邊關於 Laufey 的討論,直接說這個不是爵士樂,是 Mid-Century Pop 這樣子。另外一個英國鼓手 Andy Edwards 有一些很不同的意見,他倒是覺得 Adam Neely 也是在做一件 gatekeeper(守門員)的事情,如 Young Lions 在 80 年代做的事情:「這個是。」「這個不是。」「這個是。」很刻意很用力的要去切,其實爵士樂就是這樣,越切越小,好像一小群人才能夠玩的東西。
蘇:但譬如說在紐約,還是可以找到這些人——持續在自己的路線上,一直在走更前端的東西,像鼓手 Dan Weiss 有好多不同的 project,甚至有些是 Heavy Metal。這些東西都一直讓我覺得 inspiring,想去挑戰這個場景。
謝:他們其實都有自己的聽眾。現在會遇到這個問題,我們走了這麼久,也會知道你做什麼樣的事情,台下觀眾的反應會特別好,但你想不想要做那件事情?你要堅持你自己的 idea?還是你要 follow 著群眾、follow 著別人?
蘇:我覺得真的很難。無論在舞台上的決定、事業的決定、作曲的決定。
因疫情忽然成為「本土樂手」
謝:那麼製作面的部分,從專輯封面開始聊好了。
蘇:專輯封面找了一位好朋友、台灣藝術家胡農欣。一直都很喜歡她的作品,似乎跟我的音樂有很多連結。新專輯《自由的姿態》封面是她原本就存在的作品,她在冰島駐村的時候,拍了 28 天冰島的夕陽,光影照在絲綢布上。《自由的姿態》是關於我生活狀態的紀錄。當然都有一些小主題,但還是一直很圍繞在——我經歷這些事情的歷程。那時候跟胡農欣聊到這件事情,剛好這件作品飛起來的感覺,與我的想法滿接近的,所以做了這樣的結合。
謝:妳覺得重點是那塊絲綢布?還是光線?
蘇:一個飛揚起來的狀態,一個比較不羈的一個感覺。
謝:所以其實跟新專輯滿合的。
蘇:沒錯,就是這樣子。
謝:外面的話是這塊絲綢布,那專輯裡面的內頁呢?
蘇:那時候也在討論內頁要放什麼?後來挑到就是⋯⋯新專輯有一首曲子叫做〈Naked Swimmer〉,疫情的時候在台灣待了一年,去了一趟環島旅行,應該是台東吧?深夜做了裸泳,也是一張不經意隨拍的照片,好像是最適合新專輯的自由感覺吧?
謝:嗯嗯!我覺得這個對比其實滿好的,專輯封面就是白天,一塊隨風飄舞的布,也讓我聯想到電影《美國心玫瑰情》有一段有一個男生,拍在路上的塑膠袋,因為風吹就這樣亂飛亂飄。第一眼看到封面就想到這個畫面,代表無拘無束的自由,風怎麼吹就怎麼擺動。至於專輯裡面,妳就做一件很自由、很有安全感才會做的事情。

蘇:也考慮了滿多的,我一直有問別人說:「這樣會不會 too much?」很多人都說:「沒有啊!一點都不會。」
謝:其實還好啦!就是臉弄的模糊一點,看的不是很清楚。
蘇:那張照片本來就有點模糊吧!原本就是手機照的。
謝:妳說有些曲子是在巴黎的時候寫的,也有些是比較後來寫的吧?
蘇:有一些是疫情的時候在台灣、紐約寫的,跨著那幾年寫的東西。
謝:待台灣快 1 年多的時間嘛?生活或是音樂上面,有沒有一些什麼特別的東西長出來?如果就爵士樂來講的話,從妳出國留學開始,基本上就是待在美國,放假會回來巡演,並沒有真的與台灣的場景有太多互動。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回來,妳跟台灣的場景就會有比較多的互動。
蘇:也是滿有趣的,好像就像你說的,第一次突然成為一位「本土樂手」。真的在場景裡做大家做的事情,換不同的角度感受這件事情。

謝:假設妳都會一直待在台灣,一樣還是爵士音樂人,音樂會不會不一樣?譬如說,妳也去過很多城市,有沒有感覺到如果在這個地方,自己會做出不一樣的東西?有沒有被引導的感覺?
蘇:其實滿不一樣的。無論是回台灣或是到歐洲演出,通常一起演出的都是當地的樂手,不是我平常的團員。大部分演出的曲目,都是我自己的創作,想辦法得在這個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我傳達出去的東西大概有 70% 是原本的樣子,那其它剩下 30% 就是讓這些樂手發揮。我越來越覺得這樣是非常 OK 的。
謝:嗯嗯,以前會希望有個安全感——都要同樣的人,或者是說,即便是代班的樂手,也希望他們做跟之前樂手一樣,或是會找類似風格的人來做這件事。
蘇:現在還是會⋯⋯怎麼講,以前會更希望說,達到我原本想像的樣子。現在越來越覺得說,我要想辦法準備好那個狀態,例如在選擇曲目或是各方面,使大家有更輕鬆發揮的空間。
消失的組曲一
謝:專輯裡面的文字都是妳自己寫的。而且我記得聽妳講過,妳以前也寫小說。
蘇:我這方面一直很重視,一些超級小的東西,其實花了很多心思。譬如說,我寫文字大部分先寫中文,如何翻成英文還很像我的語氣?一直都很希望我做的文字、音樂,盡量貼近我傳達的口氣。
謝:那聲音上面呢?錄音、混音、mastering 這些東西,聲音不太一樣。
蘇:這次也是滿特別的,我找了一位混音師叫 David Torn,也是個特別的人。以前我的專輯是屬於那種聲音很乾淨的⋯⋯。
謝:這張比較 on the edge 一點,其實大家是比較擠一點。好難形容,但是該有的細節其實還是很清楚。
蘇:因為 David Torn 混音有自己的邏輯跟美感,其實滿 on the edge 不是那麼安全,特別是鼓的混音。真的有把每一首曲子的風格跟情境塑造出來。
謝:以往都是就是比較像,每一首都很接近。
蘇:要找誰混音在這方面也想很多。一方面也是因為經費的關係,現在大部分的爵士混音,好像有某種 preset 吧?反正每個樂器就乖乖的待在最好的位置,從頭到尾大概就是那樣子。新專輯就想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根據音樂的流動,David Torn 有自己的想法,什麼時間這個樂器要超級突出?什麼時間這個 echo 超級大?對我來說,也是有點驚悚的工作經驗(笑)。
謝:哈!我好像每張專輯也都在做這種事情,有些其實反應很好,有些人家會講:「哎呀!這鋼琴怎麼這樣子錄?」一些人有一套標準,一定要怎麼樣。如果說要混的很安全很簡單,拿那些好的唱片來當 reference,其實就會很安全。
-1024x683.jpg)
蘇:因為最近做一些宣傳的小影片,聽到片段覺得很有趣,加上 Dan Weiss 打的東西,腳跟手有時候並不是在同一個拍子,好像是那種 Percussion Ensemble 的感覺,空間有把它擺出來。
謝:對混音師 David Torn 來講,鼓不是一個樂器,是好幾個。這跟真的跟鼓手在處理自己 Full Set 的時候想法不一樣。音樂人的想法是這樣子,聲音工程師再把想法給加強,這是他的 idea?
蘇:這是他的 idea。
謝:他在做的時候,妳從頭到尾都在旁邊嗎?
蘇:因為他有自己特殊的工作方式,基本上是打電話、信件,當然有先溝通過一些想法。我本來就知道 David Torn 很擅長這方面的東西,他也是有滿有名的吉他手,做一些吉他噪音與很多前衛的東西,ECM 有很多他的專輯。
新專輯的鋼琴手 Matt Mitchell 的專輯都 David Torn 混的。不是那麼循規蹈矩的一個人,我知道他擅長於這種類型,也是挑戰我自己的極限吧?我決定就是讓他放手去做,我想要拉回來一點就跟他說。
謝:我自己也是做這麼多專輯之後,發現混音是真的很有趣。第一張專輯的時候會要求很多,每一首都做超久。那時的混音師是唐承運,也跟我講說:「第一次做唱片一定都會這樣子。」但是越來越到後面,我知道要用減法來做。總要到某一個時候,一定要喊停,沒有完美的東西存在。我的新專輯《Our Waning Love》,也是嘗試很多,不是很正規的做法。曲目上,我也滿好奇的是〈Liberated Gesture〉的組曲一呢?
蘇:其實是有組曲一,而且也有錄也有混。因為傳統 CD 總長還是 74 分鐘左右吧?全部錄的東西一定要拿掉一首,最後決定那首先拿掉這樣。所以是消失的組曲一,呵呵呵。
謝:可以做數位發行啊!
蘇:之後吧?如果真的不小心大賣,可能不會吧(笑)?
謝:如果妳要將專輯做成兩片黑膠的時候,時間就夠長可以把它放進去。
蘇:目前這個成品已經精疲力盡,太多東西要推了(笑)。
採訪 / 謝明諺
編輯 / 王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