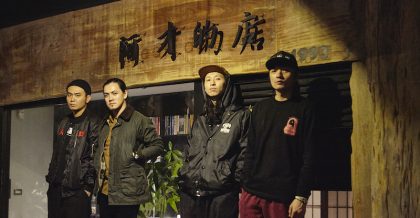2022 年尾聲,入冬的 12 月 30 日,由胡德夫、陳永淘、陳明章聯合演出的「三大吟遊詩人音樂會」,被視為年底音樂與文化圈的一大事件。這三位國寶級的民謠歌者,投注生命於音樂創作的跨度,相加在一起有近百年悠遠,與台灣的土地記憶更是密不可分,一開口就是山河雲海、歷史記憶,以及對俗世人情的脫胎智慧。他們曾笑說,這次演出唱兩小時不夠,合體後至少可以唱到六個小時。我想,他們說得還算客氣了。
負責策劃演出內容的「大大樹音樂圖像」團隊,為此投注了大量心力,在接手主辦單位客委會的委託後,從夏天開始跟拍紀錄片、安排三位歌者會面,互相造訪孕育彼此音樂的發源地——北投、關西、臺東——讓他們能全心用各自的母語與擅長的樂器,點點滴滴地合創出新的編曲。直到年底,他們又在台北的練團空間聚首、密集排練。

演出時間漸近,11 月底,在台北的練團空間裡,共同策展人鍾適芳與 David Chen(藍。掉、泥灘地浪人),正和大大樹團隊陪同三位歌手練團。彼時鍾適芳正在泰國講學,僅能透過視訊參與,她仍在線上傾心聽著每首歌排練的過程、給予務實的建議。她可能會說聲「好聽」,或言簡意賅地提醒上次的編曲進度,語調溫柔而堅定,即使遠在海的另一端,也完全不會被三位「老師」仙人般的氣勢壓過去。
運營「大大樹」即將步入三十年,鍾適芳曾和許多民謠、草根音樂人合作,包括:交工樂隊、林生祥、林廣財、雲力思、鍾玉鳳等;甚至在《流浪之歌音樂節》或《當代敘事影展》,連結來自世界各地的傳統樂人共創共演,介紹那些外於流行工業,更廣闊而盎然的音樂世界。從成立廠牌之始,即重視「由根長起」的民謠對話,由經驗具足的她與大大樹團隊策劃「三大吟遊詩人音樂會」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了。
音樂會演出前夕有許多訪談,都聚焦在三位歌者身上,關於鍾適芳和 David 如何看待三位歌者截然不同的個性,並協助他們完成這場演出的訪問卻很少。身為曾經受「大大樹」啟蒙的一員,我特別想和他們聊聊,他們是如何從旁灌溉出這場音樂會的過程。
訪談當下,天氣轉冷、綿雨不斷,適芳頗擔心年長觀眾會降低出門意願,畢竟 45 歲以上的觀眾,受三位歌者的音樂影響最深。但她仍不放棄透過各種管道,讓年輕聽眾認識他們、知道這場演出。音樂會設定了多組折扣的同行票價,以及五折的學生票,我認真覺得,能夠用這樣的「跳樓價」進到北流看這場世紀共演,實在是佛心來著。
適芳笑說,她有兩個學生在台灣,並不知道她正在製作這場演出,卻都自己買票去看,其中一位還是泰國人。另外也有指導的研究生拉了朋友買票,可能是自己教過的學生比較特別,內含老靈魂吧。以下是我與兩位策展人的訪問對話:
阿哼=哼
鍾適芳=鍾
David Chen=David
哼:台灣的原、客母語系有各自投影而生的官方政府單位(原民會、客委會)、民間創作系統,平常看起來是分開的,但在用語種分類的金曲獎上,又常常被擺在一起談。我覺得在當代尋回彼此同為台灣住民的共通性,似乎是件要緊事,想知道大大樹音樂圖像和客委會,為什麼會選在 2022 年末,策劃這場演出?
鍾:我們是今年才開始啟動(這個案子)。客委會的長鎮主委很早就有這個想法,他本來就是族群研究方面的專家,這方面的思想進步。雖然臺灣已有不同的族群委員會,他並不覺得族群事務是分離的。也不覺得客委會的資源,就只能做客家音樂,他希望可以跨部門來做這件事,把美好的事情做到。
他認為這是台灣音樂史上一個重要的大事,並努力、持續推動。因為這個計畫,我們跟三位音樂家接觸後,才發現他們各自也曾有過合作的想法。不是大大樹不居功,這個計畫的源頭是客委會開始發想並推動。要跨公部門完成這件事並不容易。
哼:一定會連結到不同部門嗎?
鍾:對,這次的主辦是客委會,原民會還有文化部共同主辦。客委會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回到你談到的金曲獎問題。我覺得原住民族語或客語都曾經歷「還我母語運動」,那個時代這些語言是被壓抑,或被貶抑,大家被噤聲許久,我們今天享受的是那個世代站上街頭要,爭取來的語言權利。金曲獎最初的語言分類,或許也是為了保障不同語言創作的自由,讓他們不會在商業競爭下被犧牲掉。但我覺得金曲的語言保護政策是階段性必要的手段,但過了一個階段後,可以思考或公開討論是否必要。如果今天金曲獎打破語言的分類,很難說誰會得對不對?阿爆可能還是能跨越語言類型獲獎。
另外就是關於歌謠的傳唱,歌謠跟語言一直是混血、難以分界的。比如說陳達的〈台東調〉好了,陳達也有原住民的血統,他最早被教唱是原住民;像客家的〈半山謠〉也是啊,他們就是混居,歌謠都不可能有分界得那麼清楚。如果我們讀鍾理和的《假黎婆》(記敘他與祖母的相處),他的祖母是祖父的續絃,來自原住民部落。文中,有一段描寫祖母進到山林中吟唱他所陌生的歌謠。歌謠其實很難分界,胡德夫在合創時會開玩笑說:「你的〈恆春調〉、你的〈半山謠〉,全都是我的!」

哼:我很好奇,這些語言應該離 David 更遙遠吧?David 作為已經完全沒有台灣母語系統背景的人,怎麼在這些民謠語言裡面找到共創的可能?
David:我一定會參考他們的詞。我會回去慢慢讀他們的歌詞,學一下背景。但是在現場,我覺得我可以不用管語言,可以靠感情。
為了這個製作,這三個月來,我一直在聽陳明章的歌,昨天也去看《再會吧北投》做功課。演出時他們沒有放國語字幕,所以我全部聽不懂,因為都是講台語,而且講很快。可是 musical(音樂劇)是講話、講話、講話,然後唱一首歌。
我非常高興有去,收穫很大,因為我在觀眾群體會到一個共同的經驗。我可以感受得到,大家哪邊覺得很好笑,可以感受到大家在哭,所以我覺得昨天的功課很有用。因為現場音樂是一個 communal experience(集體經驗),這很重要,昨天的演出提醒我們追求的是這種感覺。

哼:我去旁聽台北的練團,聽到陳明章在練歌的段落間說:「反正我們每次練團都不一樣。」David 怎麼解讀這句話?在這樣自由的表演態度裡,要去構築一個有形狀的演出是不是蠻難的,何況這次還有三位民謠音樂人?
David:陳明章說的「每次都不一樣」,我的理解是因為,他是從當下的感情唱出來的,他非常投入在那個狀態裡。對我來講,這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因為他們是從各自的家鄉到那邊碰面,聚會對他們的合創非常重要,是一個過程性的東西。
鍾:因為民謠沒有記譜,不像古典音樂,所以陳明章說的「不一樣」是因為,民謠不是一種很精確性的,很準確的。我跟 David 作為策展人,如果說參與策展有貢獻什麼意義的話,合創是我們這次特別構想出來的。
合創的過程是摸索,因為他們過去沒有做過合創。我們希望合創發生在旅行的過程裡;和過去他們的祖輩,因為遷徙而形成的音樂交集,有文化上的、歌謠上的交疊意義。
另外也希望他們可以生活在一起,有一個空間對話、做音樂。每一個音樂家對話的方式都不一樣,他們三位也花了一點時間、經過四次合創,去琢磨彼此的工作方式跟個性。但是有個東西是相同的,就是他們不會像古典音樂家,或是說像一般流行音樂把套譜寫出來,所以在玩的過程裡,可能會找出一個大概的結構跟和弦的方向,然後放出空間給彼此。
所以那個「不一樣」是,每次回來都會有新的東西,可能回家想一想,有些文化上的轉譯後,又有新的東西進來,在這四次合創裡面累積成一個結構。他們最有趣的地方正是這個「不一樣」,「不一樣」是他們的才華與音樂上累積的經驗。
哼:演出前主要有四次合創,從夏天開始。這四次分別在哪些地方?爲什麼選擇那些地方?
鍾:配合他們的工作行程,先以區域來定,第一次是在陳明章的家鄉北投,然後去了臺東跟關西。大大樹過去的一些合作,許多跟國外音樂家的合創,會在音樂家的家裡或工作室進行,因為那也是一種文化的認識與理解的過程。
三位老師雖然彼此認識,但我們仍希望創造與他們生命經驗有連結的空間,又可以容納三人及工作團隊的空間。第一站北投,第一天我們在陳明章工作室的推薦下,選擇了北投文物館。第二天在陳明章工作室,以辦桌的方式,三位老師邊吃地方菜、邊聊天、邊做音樂。
台東的話,原本希望能去胡老師的家鄉,不過因為氣候與各方條件無法配合,我們就在台東市郊租了民宿。民宿位在田間,連著幾棟舒適的廳房。很巧的是,阿淘跟陳明章都跟民宿老闆相識。我們把整間民宿租下來,三位老師、工作團隊住在那兩、三天發展合創作品。關西也是在一個山上的民宿,我們把大家困在那(微笑),有庭院、排練空間。我們儘量找到住宿條件舒服,文化上也與三位音樂家的文化連結的住處,希望他們舒服、自在地相處,同時創寫新的作品。
11 月你參與的合創,是在台北「窮劇場」的排練空間,那次主要整理最後的編曲,同時做排練的分軌錄音。
哼:在練團過程,會發現三位音樂人的個性很不一樣。陳明章興致狂放,阿淘靜水深流,胡德夫有種長者般的霸氣,但又不是全然嚴肅的人。兩位在過去很常和民謠音樂人合作,這次如何引導三位老師合創?
鍾:大大樹長期合作的音樂家,多以這樣的模式進行國際合創與合作,但這樣的模式對三位老師來說,初時需要適應,因為跟台灣音樂產業的產製工序有些不同。後來因為空間的創造,三位音樂家一起在山上、鄉間重遇與相處,音樂是重要的交談媒介,慢慢地,他們也覺得,不需要樂隊或編曲者的介入,就是三個人之間的音樂交談。
我們也期待三位音樂家能在難得的獨立的空間中,離開原本的工作模式,聽見新的聲音。我看到你有一題在問編制,最後的合創其實是非常清爽的,就只有他們三人。我們非常喜歡,因為只有三個人時,可以聽到他們各自累積的音樂力道與能量,其他的優點讓 David 來講。
David:優點很多,我馬上想起來的是「個性」。因為阿淘哥對我來講很柔軟,個子很大可是他非常柔軟,他的歌聲也是很柔軟的、很迷人的那種,唱的都是內心的。
陳明章很會唱,我蠻佩服他的吉他,很用功、非常認真,也很專心地聽其他人。他比較喜歡當 band leader,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看他跟其他不同的歌手一起互相交流,會 push 他想,要怎麼跟其他人一起做音樂。
胡德夫的部分,我跟他聊天比較喜歡用英文,他英文非常好,對我來講,他是很經典的 baby boomer(嬰兒潮)時代的人。那是世界性的民謠革命,屬於六O年代、七O年代,那個時候成長的孩子,精神上非常熱烈、熱情,也都很有趣、聰明。現在全世界沒多少這種人了,那時代的音樂家人生很有趣。他的個性非常 open,這個特色,你聽他唱歌會馬上感覺到。

哼:我自己看好像是這個感覺。
鍾:陳明章長期跟自己的樂團工作,習慣扮演 band leader 的角色,加上他個人創作型態多、演出頻繁,時間管理很好。他會把握時間、做好結論,覺得大家該練習就要練習,該把東西拿回去整理就整理好。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第一天在北投的和創,第二天早上,他已經把阿淘的專輯聽完,以及前一天想要發展的歌整理好了。前一天工作到很晚,但他回家後到隔天早上已經聽了專輯、開始整理,那時候發現,他非常有紀律。據陳明章的團隊說,他每天的工作時間非常規律,資料與文件都整理得很清楚。
我常跟 David 說阿淘是「人文畫」,他不講究工法,也不會講究器樂的技法,但他能帶出一種氛圍。他的嗓音是沒有辦法取代的,他們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陳明章跟胡德夫也常讚賞阿淘歌聲的敘事能量。阿淘開唱,他們經常會安靜地聽他唱。
我自少年時小開始聽胡德夫,對我來說,他是我音樂上的啟蒙。David 說的時代,除了受到美國民謠思潮影響,也正好是台灣民主跟人權運動進程的開始,所以胡德夫出手的東西不會那麼單薄。他經歷過的時代、扮演的身份很複雜,我不想用什麼「原住民天生就⋯⋯」,但音樂真的長在他身體裡面,所以他有時候會停不下來,在現場唱的時候停不下來,他的手只要碰到鍵盤就停不下來。

David:我補充一個有關胡德夫的。他的記憶非常好,也知道很多很多歌,我蠻佩服他的。他特別喜歡 Don McLean,我們在合創的時候,他沒事就一直彈,自由自在地唱。拿一個很粗的比喻是說,他有那個「肌肉」,因為早期的時候他一直在 club 駐唱,有發展出那種能力。
鍾:David 認為,在 club 裡面演出很久可能是一個危險的事情,那個「肌肉」可能是危險的,但我覺得他又能在危險的地方收回來。
David:為什麼那麼神奇,因為在 club 經驗外,他有自己的創作。這跟他的身份經歷有關係,參加原住民運動影響到他整個人生。我覺得時代讓他沒有選擇,一定要走過這些經驗,而很多不同的元素加起來,就出現這麼獨一無二的一個人。

哼:演唱會文案介紹寫到,胡德夫源於「山海聲響迴盪的臺東」、陳永淘來自「鄉野田園詩歌醞釀的關西」、陳明章代表「傳統戲曲和那卡西交混的北投」,都是汲取土地、歷史、口傳故事⋯⋯等養分而生的創作者。我好奇為什麼在文案上使用「民眾音樂」,而不是用我們比較熟知的「民謠音樂」?
鍾:「民眾音樂」是 popular music 的翻譯。他們三位不在一般認定的流行音樂史上面,一般認定的流行音樂很窄阿。其實 popular music 比較正確的說法是「民眾音樂」,如果用「民眾音樂」來包裹他們三個人經歷的音樂史,我會覺得比較正確,因為另一個中文翻譯有問題。
David:英文沒有分別民眾、民謠,但也有類似的問題。Folk 跟 pop,如果你想一想,所有的 pop music 都是 folk music 對不對?所以我覺得,中文有比較好分別,因為英文也是很模糊,什麼是 folk?定義太廣。
哼:因為三位音樂人的生命跨度跟作品量很大,表演歌單該怎麼挑選呢?
鍾:最早我有擬一份歌單及腳本,是從我自己的角度挑選的歌曲,但當然會提出來跟三位音樂家及他們的團隊討論,最後是尊重他們個人的情感、喜好及歌謠組合出來的敘事。
因為三位音樂家有各自的樂團組合,因此音樂會的安排保留他們自己的 set,最後一段壓軸則是三人合演、合創。合創的討論,是請每位音樂家先提出兩首曲子作為合作或重編的基礎,再接續發展。
David:前兩次合創我在美國,所以直到第三次新竹,我才加入。那時候他們選的歌已經差不多了,主要是讓他們從自然的過程去挑出來,一直實驗,一直玩,有一個公式就慢慢出來了。我覺得他們雖然彼此認識,知道彼此,但一起做音樂是更親密的一個動作。我記得適芳有很溫柔地去推動方向,稍微提出建議,老師們也會聽。
鍾:有時候啦。合創的時候是斗膽地建議,斗膽建議前面加一段什麼,或結構上可以怎麼樣⋯⋯可能之前有跟不同的音樂家合作過,也跟三位分別有過接觸,老師們理解這些建議不會害了他們。
哼:最後還是介紹一下三位歌者的音樂。因為剛剛適芳也說有挑一些歌,兩位可否各介紹三首,關於這個演出裡可能會表演的歌,或者對你們各自而言,有特別記憶或意義的歌?
鍾:我小學的時候聽到胡德夫的唱片,是我的小姊姊到了快要交男朋友的年齡,有個男生帶唱片來我們家放。那時候,大家都是帶唱片去別人家交流,我小時候也會這樣子。我記得那張唱片是胡德夫在洪建全基金會的第二張專輯《中國創作民歌系列》,裡面有〈牛背上的小孩〉。
我小時候是真的很喜歡這首歌,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刻是他的終日赤足的「赤」捲舌非常正音。可是有些詞彙對我來說是新的,比如說「那魯灣」然後「彎刀」。在那個時代,我沒有能力釐清那到底是什麼,可是它帶來了奇特的聲音。
另一首〈匆匆〉對我來說,也是記憶深刻的。我覺得參與合創比較幸福的一件事是,他們會在合創時回望、回憶,當時為什麼寫〈匆匆〉、為什麼寫〈牛背上的小孩〉等等,對我來說這些故事,重新連結我另外的生命記憶。
胡德夫的每一首經典,我小時候都能琅琅上口,他作品沒有那麼多,有些作品反覆也是重編,但卻聽不膩唱不膩,像是口傳民謠一般。你要問我第三首的話,就是〈大武山美麗的媽媽〉⋯⋯怎麼辦我沒有平衡,David 交給你了。
David:我來台灣的時候是 1997 年,不久之後,陳明章就跟金門王與李炳輝推出〈流浪到淡水〉那首歌的卡帶。我每次聽到這首歌就覺得很開心,會讓我想起那個時候。其實我是最近才看清楚它的歌詞,那個時候我不知道,那首歌當時非常流行,是一首經典。
說實在,這個計畫之前我沒有聽過阿淘的歌,所以從一個發現的角度來說,我想提他兩首歌。第一個是〈極樂〉,他用徐木珍老師送他的無音節月琴伴奏,然後講徐木珍送他這把琴,他想像徐木珍的人生是怎麼樣,非常迷人。另外一首〈阿東的歌〉,我覺得表現了淘哥的個性,很輕快,歌詞卻在講一個原住民,爸爸是山東人,媽媽是排灣族,在發現自己的祖先、祖籍的過程中走出一條新的路,對我來講,這是很台灣的故事。
鍾:其實〈極樂〉我自己也蠻喜歡的,寫作方式跟阿淘其他曲子不太一樣,其他曲子比較像 David 剛剛講的,從人事物上展開,而〈極樂〉則是從器樂開始展開,從這把琴上面他找到的音階展開,甚至最後發展出來的空間感也不太一樣。合創陳明章加入的版本我很喜歡,阿淘的專輯錄音版編寫為一首大氣派的曲子,合創的兩人版則精巧。
【三大吟遊詩人音樂會——胡德夫、陳永淘、陳明章】
時間 | 2022/12/30(五)19:30
地點 | 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表演廳
購票連結: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572429512022913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