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吳俞萱
「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不是鍾理和留在我心上最鮮明的形象。刺痛我的,是他在 1947 年 2 月 28 日寫下的日記:在台北專賣局人員取締私菸引爆衝突、士兵以機關槍掃射上街抗議的群眾之後,正在台大醫院療養肺病的鍾理和,走出病房,走向血泊:
通道上放著一具剛由五六個學生抬進來的少年的死屍。少年約十五六歲,躺在一隻綠帆布的擔架上。面如蠟蒼白,唇紫。一手放在小肚上像在深睡。臉部頰鼻額處略有塵土,黑中山服的上衣,草色褲子。被撩起著的腹部,有幾道很薄的血跡,模糊不清。子彈是由左胸乳邊入,左脅出。入口有很深的,看著就像一個黑洞的傷口,出口則拖出一顆小肉團貼在那裡像一個少女的乳頭。
刺痛我的,不只是二二八事件的暴力本身,而是鍾理和凝視暴力時,那種細膩而冷然的觀看方式:他不只看見一名「死者」,而是看到少年臉上的塵土、放在小肚上的手、那顆被子彈推出來像少女乳頭一樣的肉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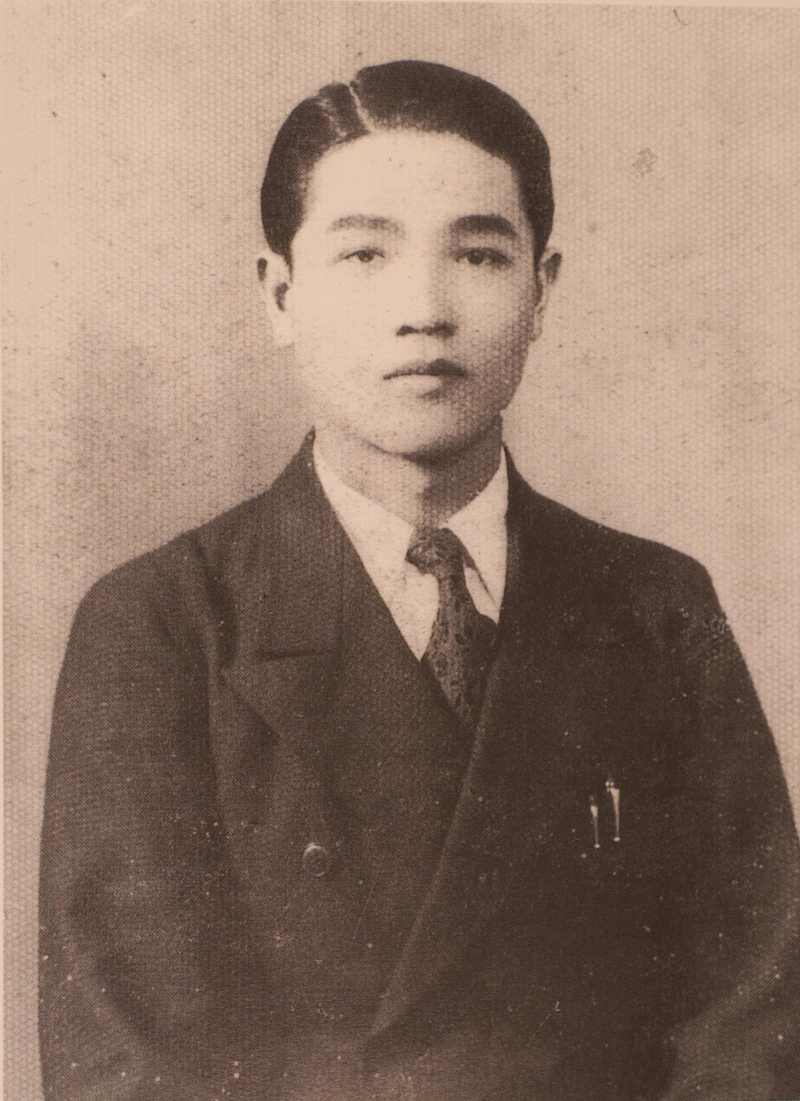
他描繪的是被暴力撕開的青春與欲望:那並存的美麗與殘酷,逼我去感覺那團肉原本正在發育,性與愛還在萌芽,此刻卻被瓦解,只剩一具被觀看的屍體。他運用近乎情色的身體隱喻來呈現政治屠殺,製造出倫理上的驚悚感。那帶著猥褻陰影的畫面,不是為了挑逗,而是把死亡的荒謬推到極致。
「像少女乳頭的傷口」不只是少年被打穿的胸膛,它同時也是整個社會被打穿的地方。
刺痛,並非來自傷口,而是記得那裡曾有燦美的生命在長――這似乎也是《大地書房》的立足點。林生祥沒有製作一張「重述悲劇」的專輯,不去放大鍾理和身世的悲劇性,而是追探他如何在貧病、戰亂、流離的悲劇境況裡一次次突圍,活出強韌的生命軌跡。
鍾理和的故鄉是高雄美濃,林生祥的原鄉也是美濃,他們唱的,是同一片土地上兩代人的命運回聲。《大地書房》的歌詞由鍾永豐、鍾鐵民、鍾鐵鈞(後兩人是鍾理和的兒子)等人共同執筆,從〈同姓之婚〉、〈奔逃〉、〈貧賤夫妻〉、《笠山農場》等自傳性濃厚的作品抽取情節與視角,再由林生祥譜曲,透過多重書寫的接力,將鍾理和的生命關懷、社會關係和歷史現場一併帶進歌裡。
從這個角度回頭看專輯內的九首歌,就更能理解為什麼《大地書房》唱的是生命,而不是傷口。開場的〈山歌一唱鍾理和〉描繪木瓜樹下那個拿筆寫字、探問時代公道的農村青年;〈細妹細妹跈我來〉專注於私奔與相隨,「就算天羅地歿也不怕」;〈山精饒新華〉以童謠歌頌古怪野性的小說角色;〈笠山農場〉則以鍾理和在同名小說結尾寫下的山歌作結:「山鳥不管人間事/猶向農場深處啼」,即使家鄉的煙樓和咖啡園已成舊事,山歌還在,勞動還在,生命沒有停下。
《大地書房》傳唱的,並非被擊穿的胸膛,而是胸膛裡那團持續在燒的火。林生祥沿著鍾理和的生命線索和文本脈絡,把創傷退到背景,把愛情、勞動、族群交纏的親密關係拉到前景;一個作家在苦難中積蓄的生命力,於是得以在音樂裡重新甦醒。
甦醒,仰賴招魂。
如果說,2010 年的《大地書房》是透過音樂,為鍾理和在美濃的山河間重建一具還在呼吸的身體,那麼,2025 年「大地書房」巡演音樂會,則是把這具身體放進一個全新的儀式場,讓它在另一個世代,再一次被請出來。
11 月 20 日,在東華大學的音樂會從一段台語朗讀開始。作家吳明益朗讀他為「美濃黃蝶祭」所寫的〈如果有人要送我一座山〉:「假使有人欲送我一粒山,我願意付予伊所有蝶仔的名,但是真濟蝶仔的名字我毋知影。」聲音一出來,不只是聽覺發生位移,從日常閒聊進入一種節奏複雜、抑揚分明的台語聲調,意識也跟著位移,被帶進一個以山、蝴蝶和植物名字為中心的聚集地:山豬肉、鼠李、尖尾鳳、懸鉤子、馬藍⋯⋯蝴蝶食草一個一個被點名,恍若一串咒語。

最後,他緩緩唸出:「假使有人欲共我講所有蝶仔的名,請原諒我心硬拒絕。因為山總是借來的,有一工,我會共家己的名放溪流。」那一刻鬆動的,不只是「生態知識」四個字,人類也位移了:原本站在中央替萬物命名的人,被輕輕推到邊緣,站到山腳、站到溪邊,改成靜聽那些名字說出它們自身。
「山總是借來的」是詩的結尾,也像這場音樂會的倫理宣言:我們並不是以主宰者或詮釋者的身份走進鍾理和,而是以「願意拋下自己名字」的姿態,走進一座借來的山、一個借來的文學世界。
朗讀之後,樂團裝咖人上場,演唱美麗和恐怖並存、呢喃和嘶吼共在的〈夜婆〉和〈仙洞〉。接著,畢業於東華大學的主唱張嘉祥說:「我在文學上受到吳明益的影響,音樂上受到生祥樂隊的啟發。」他在這一場音樂會的演出位置,也正好連結著他的創作源頭和美學視野。當生祥樂隊上台與他一起演出〈出庄〉,曲末,他用紅布條蒙住雙眼,模擬台灣道教「觀落陰」的儀式,領著現場觀眾一起大喊:「代代出狀元無?有喔。囝孫有有孝無?有喔。」
蒙著眼吹起嗩吶的他,悄悄退出了歌者的身份,化為巫者和靈媒。那刺耳又帶著穿透力的嗩吶音色,搭起陰陽之間的一座橋,為死去多時的亡魂開路――
過橋了,鍾理和。
從彼岸回到此岸,生祥樂隊以〈山歌一唱鍾理和〉迎接他。最觸動我的,是平實簡淨的歌詞勾勒他一輩子的跌宕,而生祥的曲調和聲線卻曲折蜿蜒,餘音繚繞。這首歌裡的「木瓜樹下記山河」,以及〈大地書房〉中的「一塊木板權當桌/藤椅樹影庭前坐」,都取材自鍾理和的散文〈我的書齋〉:
我家有一面寬廣的水泥庭子。數年前我沿庭坎下種了幾株木瓜,兩三年後,木瓜樹長得丈多高,一叢叢的伸張著茂密的掌形大葉。倘在晴天,樹下就有幾堆涼陰陰的樹影⋯⋯於是我搬藤椅及圓形几凳,以便置放稿紙和鋼筆水等,便在那下邊開始寫東西⋯⋯只要有一堆樹影,再加上一張藤椅,一方木板,我就有書齋,就可坐下來寫字。
〈山歌一唱鍾理和〉結尾的兩句歌詞「男人主內女主外/木瓜樹下記山河」呈現了鍾理和因病無法正常勞動,被迫「主內」,他的妻子則「主外」,背樹桁、入深山、跟男人一起扛木,在田間山路上撐起一家生計。鍾理和坐在木瓜樹下,以一種被病體和環境限制住的「內」,去打開對「外」的視野――從庭子看出去,看見田野、山川、人群、時代變遷,於是「記山河」。他能在木瓜樹下安穩落座、靜心寫字,是因為妻子在木瓜樹外,替他扛起了柴米油鹽的重量。
若把「木瓜樹」視為一種女性身體與土地的隱喻,這兩句歌詞就更清楚了:果實、乳房、哺育和庇蔭,構成一個男人得以退居「內」、化身為書寫者的場域。文學和音樂所凝視的「山河」,其實是安置在這棵樹下的山河――自然景緻、農村經濟、時代變遷與人情離合,全都建立在一個女人的體力、血汗與沉默承擔之上。
妻子的身體與勞作,替鍾理和撐出了「大地書房」這一方現實空間。因此,當生祥樂隊在台上唱出鍾理和的風骨和文采時,實際上也在進行一場對女性勞動與無名奉獻的集體追思,那個曾經支撐鍾理和得以成為作家的女人――那棵木瓜樹般的身影――也隨著歌聲一起盛放。
鍾理和倒在血泊之中,而妻子默默付出的心血,則在他的文字與生祥樂隊的音樂裡繼續流動。
音樂會的最後,生祥樂隊攜手裝咖人合唱〈風神125〉:「經濟起泡我人生幻滅/離農離土真波折/不如歸鄉不如歸鄉/母親原諒我要歸鄉/我要捨命回到山寮下/重新做人」。情感激越的時刻,回想整場音樂會的演出結構,竟然巧妙地應和了英國人類學家 Victor Turner 劃分為三個階段的「儀式過程」:分離(separation)、閾限(liminality)、再聚合(reaggregation)。先是吳明益的詩歌朗讀,引我從日常時空中抽離,再由裝咖人的民俗搖滾,把全場壓進沒有名字的過渡狀態,最終,生祥樂隊的演出與〈風神125〉大合唱,完成了「重新聚合」的瞬間。
被招魂返回的,原來不只是鍾理和,還有帶著未癒傷口、猛然記起精神原鄉的我自己。
【大地書房音樂會—東華大學】
時間|2025 年 11 月 20 日
地點|藝術學院音樂廳
特別來賓|吳明益、裝咖人
作者|吳俞萱
詩人,畢業於美國印地安藝術學院創意寫作研究所,目前在北極圈的芬蘭拉普蘭大學攻讀藝術博士。著有《交換愛人的肋骨》、《Missing》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