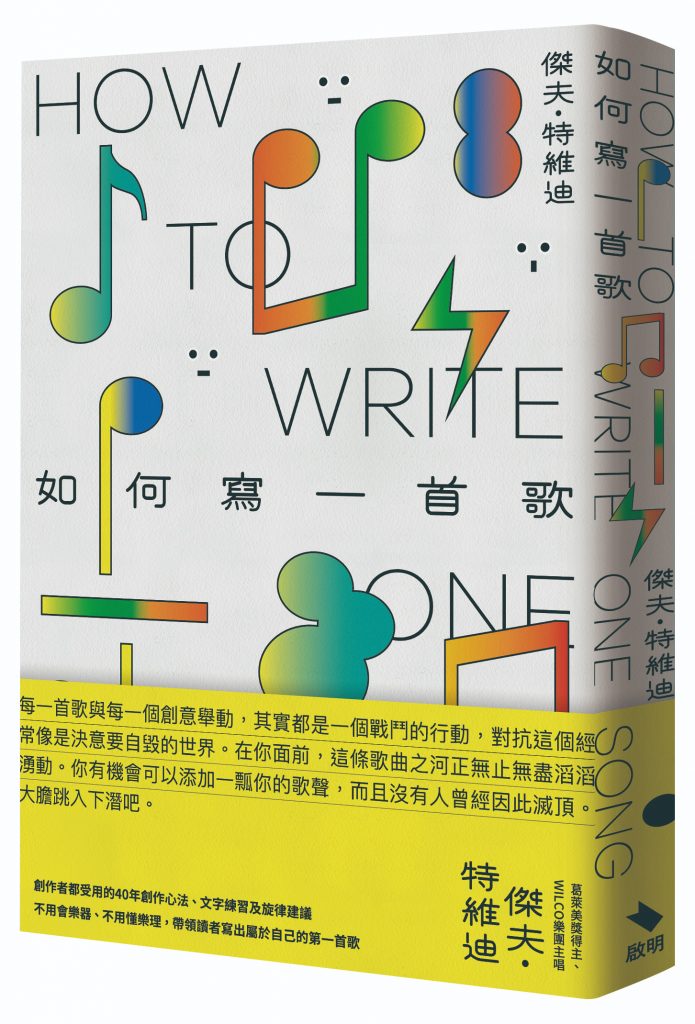文/鄭焙隆(來吧!焙焙!樂團成員,現在另一個身分是政治哲學研究人員)
「為什麼你想要寫歌?」我不記得有沒有人曾經問我這個最簡單的問題,不過我真的也有個最簡單的答案:我想要寫歌是因為我想唱我自己寫的歌。我從我十八歲開始寫歌,到現在,寫歌的日子已經佔了我人生中的一半歲月。
為了寫這篇短文,我讀了啟明出版社寄給我的《如何寫一首歌》(《How to Write One Song》)譯稿,作者是美國獨立搖滾樂團 Wilco 的主腦傑夫・特維迪(Jeff Tweedy)。這是我第二次讀這本書,我覺得對照我第一次讀原版書的印象,這個中文譯本行文流暢,也很能傳達原文的趣味,值得推薦。我期待其他朋友和我一樣因為閱讀這本書獲益良多,也感謝啟明出版社為了引介這本書所做的努力。
Wilco 是我目前為止人生中最後一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樂團。他們的音樂不取巧而流暢動聽,最初以鄉村和民謠搖滾為基底,中期作品加入些許實驗元素,近年則返樸歸真,以相對內斂的樂器演奏伴上特維迪的吟唱,我自己最喜歡他們的中期作品。正當我在修改這篇文章時,他們發行了新專輯《Cruel Country》,請朋友們去聽聽吧!
因為吸收音樂相關資訊一直都不是我的長處,我就是那種單純喜歡一直聽自己喜歡的作品的人,我特別想先提一些與 Wilco 有關的比較鮮明的個人回憶。
◇ ◇ ◇
我是在大學時候打工的咖啡館裡第一次聽到 Wilco,不過他們不是一開始在我心中就有現在那麼重要的地位。其實那時候我自己也才剛開始比較廣泛聆聽各種類型的音樂,所以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為什麼喜歡或不喜歡,說起來都有點模糊。雖然如此,那段時間我才剛開始表演,就曾和一個朋友(也是打工的同事)一起翻唱過他們的〈A Shot in the Arm〉,也從那個練習的過程中學到許多東西。
現在想起來,我那時候印象最深的應該是他們的現場專輯《Kicking Television: Live in Chicago》,這也是我這輩子唯一喜歡過的現場錄音專輯,尤其是第一首曲目〈Misunderstood〉的那個版本特別有份量,我的另一個那時候很喜歡的朋友(也是打工同事)好像還把它氣勢磅礡的前奏設為屬於我的來電答鈴。
幾年後,有一天我的一個團員夥伴告訴我 Wilco 的專輯裡他最喜歡《Sky Blue Sky》,然後也因為我想多了解我的夥伴,想透過聽出《Sky Blue Sky》好在哪來多了解他的音樂品味,這後來也變成我播放、聆聽最多次的 Wilco 專輯。
又再後來,我和另一個好朋友突然一起真正著迷於 Wilco,於是時常面對面或肩並肩坐著反覆再反覆聽他們的歌,直到那些聲響變成我們腦袋裡的深深皺褶。他們的音樂在我還不很清楚獨立音樂是什麼的時候給我啟蒙,在我需要堅定心志的時候激勵我,也在我最沒有安全感的時候撫慰了我。就像特維迪在〈Sunken Treasure〉裡唱的:「音樂是我的救主⋯⋯搖滾樂給了我名字」。我感謝音樂讓我與這一個一個朋友有了無法取代的連結,他們讓我的生命變得晶瑩飽滿。
◇ ◇ ◇
近六年前,我和團員們暫停了當時正在運作的樂團,我到國外讀書,思考一些和音樂創作基本上沒什麼直接關係的問題。用我自己的話說,我當時是,至少暫時是,放棄音樂了,因為我認為我沒有能力做到用音樂來支持我自己和團員的生活。我那時候想,無論是什麼原因讓我失敗了,既然我做不到,我也不想欺騙自己,無所謂地繼續下去。就這樣,接下來幾年我和太太及後來出生的孩子一起在國外生活,面對另一種挑戰。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幾個團員們的另一個樂團後來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我很為他們高興。
人在國外的第一年,我告訴自己,因為我失敗了,所以我要懲罰自己。雖然沒什麼特別好的理由一定要這麼做,我決定懲罰自己那一年不能接觸音樂,不過其實我還是破戒了一兩次,其中一次就是我和太太分別從各自讀書的兩個城市坐幾個小時的火車到另一個城市看Wilco。那場演出的安可,特維迪一個人伴著木吉他表演了〈Misunderstood〉,其中有一段他唱道:「沒有什麼長期目標/那裡有個我們應該去的派對/你還喜歡搖滾樂嗎?/你還喜歡搖滾樂嗎?」。
後來我看到消息, 特維迪要出版一本回憶錄,叫做《Let’s Go (So We Can Get Back): A Memoir of Recording and Discording with Wilco, Etc.》。我預購了這本書,在收到後幾天很興奮地把書讀完,後來趁過節回台灣的時候把它送給我那喜歡《Sky Blue Sky》的夥伴。《如何寫一首歌》出版的時候,我已經完成學業,人回到台灣。那陣子生活突然沒什麼重心,有點輕飄飄的,我把這本書下載到電子書閱讀器裡,快速看完了(然後把它推薦給另一個夥伴)。我很高興,因為要寫這篇文章,讓我有機會把這本書好好重新讀過一次。
◇ ◇ ◇
顧名思義,《如何寫一首歌》這本書旨在幫助所有想要寫歌的人寫出一首歌。而無論過去如何,我們現在要寫的這一首歌將會是未來可能出現的其他所有歌的起點。
那麼在寫歌這件事上,特維迪有給我們讀者一些直截了當的建議,包括叫我們別拖延和逃避(當然了!),也提了一些非常具體讓我們可以參照執行的方法。比方說,特維迪叫我們隨意翻開一本書,單純是為了尋找吸睛的詞語,然後試著對它們排列組合,找出它們的聯繫,賦與它們新的意義:也就是,把它們變成一首歌的一部分。又比方說,我們也可以從與身邊的人的日常對話中截取詞句段落,一樣用寫一首歌的方式賦與它們新的意義。哇,這就是創作!
對這些可以直接嘗試挪用的技巧,我就不多說了,想邀請朋友們自己去吸收、探索特維迪的妙方。我相信,這些嘗試不只能幫助我們寫出一首歌,也能讓我們對音樂有更深刻的領會。就特維迪看來,這些方法之所以有效,正好是因為它們扎根於我們的生活。畢竟,我們唱歌不就是為了用我們喜歡的方式說我們的故事嗎?
此外,特維迪也強調,無論我們把寫歌當做工作還是興趣,創作不只需要有靈感,也需要我們花時間和力氣投入那個創作的過程。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工藝,必須奠基於我們的反覆練習、琢磨。所以他說:「本書的基本前提是協助你找出一個創作程序,並發掘出讓你沉浸其中的意願,以便讓你的創作過程,足以可靠地催生出一首歌」。
用我自己的話來說,這個創作程序的核心是:不停地用任何自己覺得有趣、有效的方式嘗試創作,並設法從嘗試的過程中萃取自己覺得有價值的成果。特別的是,特維迪認為,我們能從不斷嘗試的過程中創作出作品,這是因為:我們不只是能有意識地從尋常生活中挖掘出有意思的材料,並對它們做加工處理。在某個意義上,我們的潛意識會自行運作,隨時對我們接受到的資訊做出恰當的反應。
因此,作品其實反映了我們作為創作者的獨特自我,這就是為什麼看似隨機的創作嘗試通常都有其道理。所以特維迪寫道:「我相信,你需要有意識地把自己送上潛意識的道路上去。」雖然創作者也必須有紀律地工作才會有成果,特維迪提倡的並不是一種有標準化程序的生產:他「渴望造出樹木而非桌子」。
進而言之,在創作時,我們其實也是在塑造自我:
一棵樹,幾乎可以意指任何東西。一棵樹,基本上就是⋯⋯我。 我是一棵樹。我無法完美地塞進任何的模子裡面。我也不是經由一組特定計畫所打造出來的人。我在人生中所遭遇的大小事,已經打磨掉了那些鮮明的稜角,將我塑造成了一棵樹──將我塑造成某種較難以預測、也較難以理解的事物。
讀這段話讓我想起,當我們遭遇創作瓶頸想互相激勵時,我曾經問那個與我一起非常著迷於 Wilco 的朋友:「你是一把劍嗎?」我想問的大概是:你的心神是不是足夠銳利,以至於能用創作劈開那些無所不在的陳腔濫調?
說實話,我想在某些層面上,我大概有點抗拒特維迪給出的創作觀和人生觀。作為一個崇尚理智的人,我時常希望我能用自己能完全把握的方式完成我的作品。也因此,我覺得我的自尊不容許我接受他的那個說法,也就是我必須擁抱我的無意識以獲得更好的創作。
◇ ◇ ◇
《如何寫一首歌》雖然是一本要幫助讀者創作出歌曲的書,但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作者特維迪用各種自身的經歷為引子,精采地描述了他如何理解他自己大半輩子埋首於創作的人生,或者說他的人生與創作之間的關係。
讀著這些小故事大道理,也許會有其他讀者像我一樣,簡直不太能相信特維迪就是這樣一個誠摯而溫暖的人。直到現在,我依然偶爾覺得,當我把特維迪想像成一個正在受苦的藝術家時,我最喜歡 Wilco 的音樂。作為樂迷,我想像他們的創作過程應該要很激烈吧!我總是以為,我應該要記得特維迪在紀錄片《I Am Trying to Break Your Heart: A Film About Wilco》裡在混音室與當時的另一個夥伴針鋒相對,然後到廁所嘔吐的畫面。
讀完特維迪的兩本書,我知道我搞錯了。無論當時他覺得身邊的夥伴有多惱人,他終究相信,比方說,準時與禮貌才是很酷很搖滾的事。他也說,雖然他心裡多少也還是有「你必須備受折磨,才會出人頭地」的迷思,「不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每個人其實都在受苦。」他的結論是,是否執著於生活中的苦痛並不是重點,重點是動手做:動手創作。
已經三十六歲了,我還是會希望能有人指引我,幫助我往好或對的方向前進。如果我說讀這本輕薄短小的《如何寫一首歌》讓我對人生有新的大領悟,那可能真的太誇張了。
不過身為樂迷,我當然很高興能看見特維迪自己現身說法。我因為他直接、詼諧而不裝腔作勢的口吻而感到親近,我也覺得他願意身體力行的準則通常都十分有道理而值得我們學習。在我們特別佩服的人之中,有些人可能是我們的偶像,而另一些人或許可以是我們的榜樣。我們的偶像在我們眼中有神奇的光彩,因為他們用我們無法想像的方式變成我們非常想變成的人。相比之下,正好是因為我們的榜樣為我們展現了各種可能性,他們是那些值得我們學習、效法的人。
◇ ◇ ◇
和許多人一樣,我因為聽到很棒的音樂而渴望創作:喜歡音樂,想唱自己寫的歌,想寫出很棒的歌。然而後來有好一陣子,我覺得我迷失了,不太確定自己是誰,也不再覺得唱歌或不唱歌的自己有什麼差別了。我覺得我好像必須得到處發一張張假想的名片,名片上列舉了我寫過的歌,然後說:「你好,這些是我的歌,拜託你喜歡我吧。」但其實我大概也並不真的那麼喜歡、滿意那些歌,結果是,我也不真的那麼喜歡自己了。到底是什麼讓我在那幾年放棄了自己,陷入自我懷疑?如果要我自己做個總結,我會說,或許部分也是因為我太想寫出很好的歌,反而被那願望壓垮了。現在的我,渴望能找回初心,找回那個曾經著迷於音樂創作的自己。
因為體驗過那樣的不斷自我批評,讀特維迪下面這段話,讓我特別感動:
我認為,當人們可以走出所謂的社會階層與身分之外,沉浸在「為藝術而藝術」的個人時刻之中,這將是舉世最酷的壯舉。對於人生的最終目標應該是什麼,假使我們能夠採取務實態度的話,那麼,不帶雄心壯志、只是直抒胸臆地去進行創作,或許是每個人可以嚮往的最純粹之事。
我們大概都聽過「為藝術而藝術」這個口號,我們也知道它告訴我們不應為了功利或其他與藝術自身無關的目的而創作。但特維迪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要寫歌,我們甚至不一定要寫一首好歌。如果我們想要寫一首歌,那麼就去動手寫一首歌,去享受寫一首歌的過程和成果。為了寫一首歌而寫一首歌,這可以是一件最純粹的事情,也應該是一件最純粹的事情。
(傑夫・特維迪《如何寫一首歌》,啟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