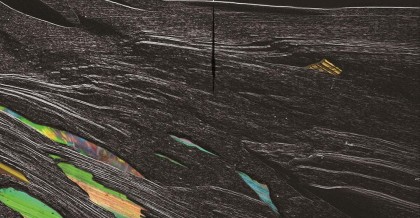據說成團 20 年的非人物種,離團的成員超過 20 個。
那麼音樂風格呢?樂團簡介裡,如此寫道:「四人無賴樂團,從音樂到演出除了任性還是任性,試圖組合團員們的品味及各種元素,並以 emo 的方式表達。」
這次採訪開始前,經紀人 Bully 特別提醒團員,等一下訪問要帶到明年 1 月 7 日會在台北 Legacy 舉辦專場。他們真的有帶到這個日期,但跟新專輯《珍饈》的事情一樣,僅是點到為止。
我先說,這不是一篇「主流」的專訪(字數約如李靚蕾的五千字長文),一切脫稿演出,不必期待他們融入預先準備的題目。
以下的對話,(大概)就是非人物種成軍 20 年、離團 20 人的 vibe。

總之那天晚上,我這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走進主唱阿顯開的店,喝著事先買的啤酒。短短的 40 分鐘,有一搭沒一搭說些幹話。笑聲跟尷尬靜默的時間比大約是二比一。
「〈擺渡人〉MV 封面女生是誰?」開場問完這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並得到答案後,我低頭瞄一下訪綱,想說從簡單的題目問起比較好回答。「那講一下成團的過程好了?2001 年開始?」
「2001 年,我是大一啊。」貝斯手撥屎說。
「阿顯是幾年加入的?」我問。
「2005、2006 年了吧?」撥屎說。
「24 歲,我記得是當完兵啦!」阿顯說。
兩位待最久的團員,對團史的記憶似乎有一點出入,因為展開答辯。我按照某種慣例追問下去。「所以那時候玩什麼?龐克?cover?還是開始就在創作了?」
「應該是沒有 cover 過吧?亂弄一通吧?」撥屎詭異地笑說。「什麼風格喔?古典交響金屬。」
笑完現場沈默了一會兒,窗外經過的摩托車聲都能清楚聽見。站在一旁的是攝影師張修齊,混跡地下音樂場景多年,非人物種的 EP《真善美勒?》封面即由他掌鏡。大概是想讓空氣再輕鬆一點,他暫停手邊的拍攝加入對話:「2001 年,來宥丞在幹嘛?」

來宥丞是鼓手阿來的全名。今年 29 歲,穿著打扮看來剛下班的白領,跟另外 3 位成員相差十歲。他在上一張專輯《直白一點》加入非人物種,目前還參與其它樂團,像熱寫生與 MassMan。
「2001 是 20 年前,20 年前是我小三的時候。」阿來說。
「所以 2001 年,剛組團的時候。」
「他在看《忍者哈特利》。」
「那你有看到爸爸偷藏的 A 片嗎? 」
「沒有耶,我那時候⋯⋯是高中的時候,我朋友拿 Sony Ericsson 的手機,然後那個螢幕也很小。」阿來用手比出一個大小。「然後看那個蒼井空的,就覺得 WTF。」
阿來笑說,第一次有種「誒,這段不要剪進去了」的念頭。訪問通常都是撥屎與阿顯講一些有的沒的,他會一旁煽風點火。沒想到這次角色互調。
「我們現在人設是,我們是愛看那個《尼羅河女兒》。」
阿來這段話提醒團員,訪完得穿洋裝,拿著上頭印有小狗,有浣熊,有貓頭鷹的氣球拍照。
接著,話題從《秀逗泰山》、四驅車、港漫、解碼器聊到第一次抽菸,瞎聊這些比音樂上的事情來得放鬆且真實,這大概才是非人物種吧?我想了一下,決定將訪綱放一邊,卸下身為訪問者的身份(這時候訪問大約進行至三分之一)。
「哎,你們氣場太強大了,讓我覺得問這些問題很白癡。」
「鄭光顯只是不好意思直說啦!」撥屎說。
「蛤,什麼什麼⋯⋯」阿顯說。
「不知道問什麼。」我說。
他們說還是可以訪一下。
撥屎這時候問阿顯。「誒,鄭光顯,你第一次喝掛是什麼時候?」
「忘記了⋯⋯。」阿顯說。「喔!退伍那次,生日去地社(地下社會),然後被 Dizzy 抓到。」
「我在嗎?我應該不在。」
「你在。」阿顯記得那時候,所有人都跟他說:「幹!你生日敢來地社?你完蛋了。」然後被同樣是空軍的學長 Dizzy 抓到,他就喝掛了。
「楊智明咧?」撥屎問。
「蛤?」
撥屎突然被團員嗆。「等一下等一下,你是主持人是不是?」
「不然怎麼辦?」撥屎說。
那就繼續講些五四三,我嘴巴沒說,但內心是這樣想的⋯⋯
「你的訪綱呢?」
「大牌主持人不需要訪綱。」撥屎模仿一個奇怪的聲調:「你們需要一個曝光的機會啊!」
「龍套在那邊⋯⋯龍套需要講黃色笑話搏版面。」
「不然就要穿泳裝,不小心露點。」
「差不多,穿著洋裝在這邊講第一次看 A 片的事情。」阿來笑著說。
再度沈默了一會,等著有人開口說話。
我想說,不然就問問看新專輯《珍饈》:「那不然就介紹專輯好了,好不好聽?」
「還好。」他們回說。見仁見智。看我想不想聽。
「你有好奇什麼事?」阿顯反問我。
「我還好耶。」我說。
「那這樣怎麼辦?」
「對啊,那這樣還要訪什麼?」
「好啦,介紹歌啦。」我說。
「我們要介紹什麼歌?」
「〈美蘿〉好了,美蘿是在 2017 年開的咖啡廳?那時候在民生社區吧?離我家蠻近的,因為我國小念旁邊,可是我沒有去過。」我挑了這首聽來很有九O年代流行龐克味的歌,當美國 YA 片的配樂不違和。
「那首歌喔⋯⋯寫什麼?就寫那時候一個感覺,就是大家很愛玩。」阿顯說。
「為什麼後來關掉?」
「因為大家都在玩啊,那個點本來就很難做,就覺得時間差不多了。」
「現在這邊有比較好做嗎?」
「還可以呀,順順的。」
撥屎嗆阿顯不好聊。
「現在這邊還不錯啊,就是撐得住啦。」阿顯說。
然後又沈默一會。
「還有歌要講嗎?歌都以前寫的喔?還是現在寫的?」我問。
「歌就是這兩年陸續寫的。」智明說。
「都是新的歌?」
話說這兩年,非人物種表演跟錄音同時進行。今年初,打算發行專輯,無奈碰上疫情爆發只好延到現在。
「對啊,就寫了兩年,所以就是這兩年,我們發生一些的事情。」
「像團員離團嗎?」
「對啊。」
「沒有啦,這兩年也沒有人離團。」
吉他手智明,長得有一點像台通何ㄟ。不知道白天是從事什麼工作,但玩團經驗應該蠻豐富的。大概是 2017 年的時候加入。在這之前,對於非人物種的印象就只有代表作〈擺渡人〉與「團員很愛吵架」。新專輯《珍饈》能聽見他對於九O年代另類搖滾與台式搖滾的造詣。
「有些歌的 idea,可能是我加入前就有了。然後大概前年,我加入之後,就把那些歌慢慢做。可能做了兩三首就去錄音室錄起來。 」智明說。
「這張專輯是你們四個一起做的,都有參與到?」
「對。」
「你們去哪裡錄的?」
「玉成。」
這一段對話,是比較有聊到《珍饈》的製作層面。我簡單整理一下,大概是說,他們本來製作人想要找玉成錄音室的錄音師 Andy Baker,彼此的 tone 調蠻合的。可惜 Andy Baker 沒要當製作人,但還是有給一些想法,彷彿是第五個團員。
「那錄多久啊?也是錄兩年?慢慢錄嗎?」我問。
「錄差不多兩年。」
「錄音的時程大概就是我們寫好歌,去錄一個週末,錄三、四首。然後分好多次這樣子。」
「大概錄了 20 天。」
「七百多天裡面有 20 天在錄,好像沒有很認真的感覺,直接寫錄了兩年好了,比較酷。」撥屎笑說。
聊完新專輯之後,我還是丟了沒在訪綱裡,又稀鬆平常的問題:「為什麼團名會叫這個?誰取的?」
「那要問創團元老。」後來才加入的吉他手智明,接下這個問題後,丟給撥屎。「是你取的嗎?」
「不知道,你要再聽一個版本嗎?」
「不然你再講一個新的版本。」
「好!我想想⋯⋯你們先講下一題,我想到再跟你講⋯⋯。」撥屎說。
「欸!我沒有聽過最原始的版本。」
「啊你自己上網去⋯⋯每個訪問都要問這個,很煩,我想一下⋯⋯。」
撥屎接著漫不經心地說,團名是霞海城隍廟求籤得來的。「四行,然後第一個字湊起來剛好『非人物種』這樣。」
「新的專輯有人問過這個了喔?」
「已經很久沒有人來訪問了啊⋯⋯。」
「之前訪是什麼講過啊?啊,見證大團的陸君⋯⋯。」
「之前好多都有,然後那個訪綱來,叫我們寄回去就那個⋯⋯隨便啦,各自解讀啦。」
這時,阿來可能想到什麼,突然說起青山祭,那天他與司機在車上對話。司機問他:「啊,你這個是樂器嗎?你們的歌在 Spotify 上聽得到嗎?叫什麼?」他回:「可以喔!叫做非人物種。」
那位司機再問:「不是人喔?啊是什麼?動物喔?」阿來回:「對啊!應該是動物吧!」
「所以是小兔子嗎?」
「對,還有小貓、小狗。」
「啊,你們這個小兔子、小貓、小狗的音樂是怎樣的?」
團員大笑完,撥屎補了上一句:「就是在你惡夢裡面會出現的小貓⋯⋯。」
解釋一下,我會問團名的由來,是因為「非人物種」聽來很像導演 John Carpenter 或是反烏托邦的電影中譯片名,私心期待有什麼關聯。又想到這位司機假如去 Spotify 搜尋非人物種,然後又看到他們穿洋裝拿動物氣球拍照的專訪,不知道有什麼想法⋯⋯
「反正全都誤打誤撞出來的。」阿顯說法跟撥屎差不多,團名誤打誤撞,歌誤打誤撞。我這篇訪問也是誤打誤撞。
接著引發一陣對於團名的討論。他們認為組團的時候,取團名根本就沒什麼意義,帥就好了。不過千禧年前後,三個字的團比較多,像是牛皮紙、碎紙花、薄荷葉。董事長樂團甚至還跟撥屎說:「團名要三個字比較好。」但現在好像是四個字比較多。
「傷心欲絕、美秀集團、落日飛車、湯湯水水⋯⋯。」撥屎說。「專輯名字應該也沒有意義啊,我覺得。」
「〈離開有意義〉嗎?」我刻意用他們新歌名稱當成哽。但其實這是首好歌。
「我覺得『旅行』才有意義。」撥屎接了這個哽。
阿顯補充說明,那時候出發點都是覺得要好玩,要帥。「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沒有那麼多有意義的成分在裡面。然後都是越走⋯⋯我覺得可能團名取出來之後,團名跟團格就會越來越合在一起⋯⋯。」
接著又停頓一下,我算一下大概是十秒鐘。
「還有什麼要說的嗎?」我說。
「我們好像也沒什麼要說的。」撥屎說完突然想到經紀人訪問前的提醒。「喔,那個啦!我們 1 月 7 號要專場,對!」
「那票還賣得好嗎?」
「票賣得快差不多了喔!大家趕快買喔,不要扼腕喔!」撥屎像是對著鏡頭叫賣。
「如果這個時間還沒有差不多了,那⋯⋯。 」
「那這個團就⋯⋯。」
「我們那天有類似太陽馬戲團之類的,一些節目安排。」撥屎笑著說。
專場話題聊到這裡打住。他們與經紀人 Bully 突然好奇起這篇訪問會如何呈現,反問我剛剛對話的內容能不用之類的。
「我想給別人寫。」我說。「可是我不知道別人有沒有辦法寫。」
「啊是不是因為我們很常四個人同時講話這樣?」
「不是不是,是沒有講到可以用的。就是我現在會快速判斷,有一些可以用的素材。」Bully 覺得目前聽下來超ㄍㄧㄥ的。
話說完,團員拱他當主持人。我也順水推舟。「不然你幫我問一題就好。」
「我來想一下。」Bully 沒有問團員問題,卻提供一個脈絡。「我自己在外面看,不論做音樂或現在這個團。我覺得對他們來說,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包括其實從一開始,他們其實並不是說,預設要玩一個團、要寫什麼歌。」
因此很難將問題聚焦在非人物種的團名、專輯概念,因為 Bully 猜是沒有這些東西的。他認為,這是他們生活的展現,隨著時間越走越遠,那個意義就會顯現出來。
「所以其實蠻需要,比方說採訪者,或者是他們身邊的工作人員,去幫忙抓到或釐清這個脈絡。因為你對一個做這件事很自然的人來說,他很難去講,他怎麼會游泳?怎麼會寫這些歌?你問他就說:『喔,就是那時候生活的感受。』」
「以後採訪就 Bully 一個人去就好。」撥屎說。
「那你們覺得 Bully 說得對嗎?」我問。
「但〈離開的意義〉確實是有在寫一些東西啦。」阿來說。
「寫一個心情啦,也是一個情緒啦⋯⋯那個當下,除了大眼以外,還有山羊。」阿顯說。
「是因為山羊那時候要收了,所以才寫這首歌嗎?」
阿顯解釋,非人物種有一個慣例,每年一月都會去墾丁的山羊飯館表演。對於平時都在上班的團員來說,這是他們的假期。「那一年,吉他手大眼要離團,最後一場是在那邊。然後同一年山羊也收掉了,就是寫這個心情。」
不是很清楚大眼為何離團,或是他們在山羊飯館發生過什麼事情。但我也都不想細問。
「你們現在四個人,也是會吵嗎?」我問。
「我們四個喔?比較常吵的,其實應該算是我們三個吧?」撥屎說。
「應該只有我沒吵過而已。」智明說。
「為什麼你不會跟他們吵?」
「因為我菜鳥。」
「不是,因為他是婊子啊!」撥屎笑說。「婊子不跟別人建立深厚情感啊!」
「你少在那邊啊,你自己也是婊子。」智明對阿來說,兩人現在婊的程度一樣,同樣有玩其他樂團。
「我每個都放感情,放太多了。」阿來為自己辯駁。「主要還是在吵音樂上的事情,因為不通順的地方很多,想要把問題釐清。就沒有人很有經驗。」
「因為有些人,我覺得可能音樂很懂,可是他不太會跟人家講話,他就用音樂上的方式去表述,可能這關就過了。啊我們是相反,我們很會講話,可是我們在音樂上不太會講。所以有時候,在音樂上撞的時候,就會在那邊一直繞,到底要怎麼去把這東西解開,反而就會戳到對方,這樣子。」
「我自己是這樣(迂迴?),但其他人的想法可能是『啊幹,我就是很直接』,大家的個性不太一樣。但是我覺得,現在四個人的共同點就是會有一個衝動。」阿來說。
「我沒有。」智明說。
雖然,智明嘴說沒有,但阿來覺得,他看智明的表演有衝動,所以才會想把找進非人物種。
撥屎則繼續補刀。「進來之後就這樣了,他(智明)就是歷經了一段深刻的感情之後,就再也不放感情的那種人,開始成為一個婊子。」
「欸,有道理耶我覺得,你這樣講蠻有道理的⋯⋯有戳到什麼嗎?」阿來說。
智明同意大部分都是吵音樂上的事。
「而且生活高高低低的,有時候。」
「低潮還會開始遷怒。」
「對,大家都有自己的狀況,然後我們又是公私不分的樂團。」阿顯說。
公私為什麼會不分?他們的答案是,因為這個樂團沒有在賺錢。這應該是中型、小型樂團,或是「中老年樂團」都會碰到的狀況。
「當你樂團帳面的收入到一個程度,可能有些事情就吞得下去。」
「那時候就會有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吵的內容是不一樣。」
我問同時有玩別團的阿來。「你覺得他們特別會吵嘛?還是還好?」
「超會。」阿來毫不猶豫地說,非人物種特別會吵,而且很會戳人痛處。「看到你那邊有爛瘡。他們一定要把它割開,把它擠出來,然後踩兩腳。」
「就是要把那個毒趕快先擠出來,傷口才有辦法趕快好。」阿顯說。
「你一直爛在那裡也不是辦法。」撥屎說。
接著,撥屎與阿顯,兩人幾乎同時說,就是要灑鹽、消毒。被另兩個團員虧超有默契,不愧是吵架次數最多的團員。
「但是非人物種應該⋯⋯。」智明說。「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在台南,就是跟南部人玩。南部人都很直接,譬如說你彈不好,就會直接講『幹!你他媽在彈三小』。」
總之退伍回來台北,智明很不習慣,他覺得大部分台北團都不敢把問題講出來。「譬如說我彈超爛,他們也不會跟你講,可能就不說話,然後很迂迴。」他覺得加入非人物種之後,又回到以前南部玩團的感覺。
「真的嗎?我們有很直接講嗎?」阿來說。「我也覺得我們是迂迴,我剛剛想要表達的就是這個。」
「來宥丞是迂迴,但他的表情跟動作都會表現出來。」撥屎模仿阿來打鼓的表情,邊虧邊用他的語氣說:「(你)這個 solo 還不錯啦!」
「還是有迂迴成分啦。就是比較之下,非人物種團員間都還是比較直接一點。就算他不講,你也看得出來。」智明說。
阿來一直有注意到這事,覺得玩樂團玩這麼久了就「順順的」,但其實還有卡卡的感覺,後來去錄音之後才發現,「幹!就是沒有『釘』人你這樣子,沒被『釘』。」
阿來這時拿了放在正前方桌上的訪綱看了看。
「有什麼想要分享的都可以,還是你幫我問。」我應該是邊說邊掏錢包,想用實際行動表示心意。
「誒,可是其實⋯⋯今天訪問狀況算蠻好的,以前訪問如果沒有這樣瞎聊,大家也就是很尷尬。」智明說。
阿來覺得我也是想要好好問,又不想問一些很普通的問題。
「沒有沒有,我沒有很想問。」想不到我的表現竟然被肯定,打開錢包看裡面剩一張一千塊,一張一百塊,拿了一百塊給阿來,但被拒絕了。
「他時薪不只這樣,而且那低於最低工資。」撥屎說。
「誒,我剩兩張而已耶。」我說。
阿來試著念出訪綱上的問題「隨著年紀增長,持續會想要演出的動力是什麼」?他說有時候也會想到這件事情。「我們玩團已經這樣子了,很多好笑的事情看過了,爽是也爽過了,持續想要演出的動力是什麼?」
「慶功宴啊。」撥屎說,每次慶功宴都會有不一樣的難受。
「所以你現在最想要的感覺,就是比如說,你那次演完的慶功宴,身體跟心理狀況都超好,假使有一個這樣的狀況。」阿來像是心理醫生,試著分析撥屎的想法。
「你就想要達到那個涅槃。」
「你天堂了,然後那你接下來還會想繼續演?」
「不是!你射精了覺得超爽,但不可能只射了一次,你就不再射了吧?」撥屎說,假設昨天打了一個超爽的手槍,然後再也不打了嗎?不就想再去追求那個很爽的手槍?
「人事時地物這樣?可能找別的片這樣子,尋求新的手法、新的甜蜜點。」阿來換問阿顯。「那你呢?持續演出的動力是什麼?」
「就好玩。」阿顯說。「對啊,其實是差不多的感覺,跟大家一起做事,然後台下看到很多人。」
「然後 show fee 還不錯這樣。」
「如果還不錯的話。」
「可是我覺得那個只是一個重點,我寧願 show fee 很不錯,然後台下沒什麼人。我也不要台下很多人,然後我們沒什麼 show fee。」撥屎笑說。
「智明咧?隨著年紀增長,持續會想要演出的動力?」阿來邊問智明邊說,等一下要去開會了。
「因為他是個婊子,持續想要受人注目啦!」撥屎說。
「你有想要受人注目嗎?」阿來問。
「還好誒。」智明說,就很喜歡彈樂器,還有點感性的透露。「加入非人算是我玩樂團生涯一個轉捩點。因為那之前就跟團員吵架,本來有點想東西賣一賣就算了。」
「那個時候不想玩這樣。」
「算是有點被救到。」智明說。「結果後來變婊子,不知道為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很生氣?他都跟別的團員吵架,都不跟我們吵架。」撥屎說。
「你吃醋喔?」
「我那時候看他沒團,然後找他來之後,媽的,現在每個團⋯⋯。」
「都要啊。」
「你像老鴇就對了。」
「你說我喔?對啊⋯⋯我先去準備一下開會。」阿來起身離開。
「誒,我們也可以一起去嗎?」撥屎說。
「好狡猾,自己不回答。」
我想不宜拖太久。「那這樣好了,拍照好了!」
「拍照嗎?結束了嗎?」智明有點驚訝的問。
「結束了。」我跟著站了起來。
「那有什麼問題。」撥屎說。
你知道他們專場是什麼時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