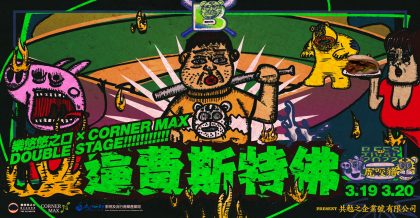7 月 31 日週五晚上撐著時差,人在紐約 Fidi Creatives 文化空間聽 Taiwanese Waves 與亞洲創意基金會(Asian Creative Foundation)舉辦的前導講座。主題是「母語創作」,講者包括參演 Taiwanese Waves 的鄭宜農、阿爆(阿仍仍)與那屋瓦少女隊,以及來自巴塞隆納的音效設計師 NOIA、馬來西亞籍歌手 FIG。
在美國聊這題,即使有主持人協助雙語翻譯,多重語言卻仍像在空中打架、線頭交纏。情況可能是,那屋瓦少女隊用華語介紹族語再由翻譯講成英語,或者 NOIA 用英語介紹加泰隆尼亞語再由翻譯講成華語。
翻山譯海,資訊來往於場面難免混亂,主持人王宇平(Vickie Wang)是喜劇演員也做口譯,具高度專業仍有一度糊塗把「FIG 的英語翻成英語」。大家聽著笑著,大概也就了解,這處的第一語言串接母語又再繞向另處的第一語言,是這麼燒腦這麼難。
語言卡卡,用心表達,講座依然有突破壁壘的時刻,好比曾妮舉例排灣族語的婉轉特性時說,他們不會直接講「礙眼」,而會說「這朵牽牛花的汁噴到我眼睛了」,透過英譯逗樂全場;或者 NOIA 說,她想教自己的孩子加泰隆尼亞語,即使不一定「有用」,語調真摯且感動。
講座尾聲更見「大場面」——當真愛領唱布農語歌謠,用歌聲繚繞全場,只見不分國籍、膚色的 50 名觀眾都跟著哼唱、拍手、搖擺。當中坐在最前排,唱最大聲的,甚至有許多本來是為追宜農而來的中國粉絲。
「音樂超越語言」這句話聽過很多遍,但在這親密的小空間再次見證,仍覺得像魔法,讓我一度忘記時差。而這魔法,過兩天又將在紐約中央公園 SummerStage 以更盛大的方式重現。
邁入第九年、第六屆 Taiwanese Waves,相隔兩年重返 SummerStage。由「紐約媽媽」嚴敏策劃,今年名單邀請鄭宜農、阿爆與那屋瓦少女隊、布拉瑞揚舞團,三組共演。「母語」主題策展方向,頗有呼應 2017 年以滅火器、桑布伊、黃玠與黃小楨,分別呈現台語、族語、華語的獨立唱作陣容感,然而今年因為舞團的加入和整體電子風格調性,反倒更像是把聽感與身體當作推進器,外延語言的包容度,不僅止於母語而已。
8 月 3 日下午,阿爆與那屋瓦少女開場先以〈Empire State of Mind〉的「In New York」齊唱迎賓,再於〈1-10〉裡屢屢喊出「Tawain」的名。台上唯一樂手是多年合作的明馬丁 Musa,獨立玩轉節奏類型音樂 non-stop 歌單,讓阿爆與少女隊毫無顧忌地接力原創、翻唱、古調曲目。
語言有排灣、阿美、布農,甚至英文、台語、華語歌,在舞曲後的 acoutic 段落,他們各自翻唱了福音詩篇、山地情歌〈白米酒〉、江蕙〈家後〉、陶喆〈普通朋友〉、梅艷芳〈親密愛人〉,甚至小賈斯汀的〈Baby〉,以此銜接布拉瑞揚舞團的《#是否》的原音風格組曲。
當〈拒絕再玩〉、〈Bad Boy〉、〈愛情比你想的閣較偉大〉、〈燃燒吧火鳥〉等歌曲,被持麥唱跳的原民舞者群情演繹,部落卡拉 OK 沸騰的生命力,讓整個紐約 SummerStage 一度與千里外的台東 Pasiwali 音樂節疊影且毫不違和。
有意思的是,那屋瓦過去一年出演國際舞臺,都會創作一首呼應當地曲風的歌。在紐約,他們也引用臺灣國際電話區號「+886」寫了一首頗洗腦的〈886 Waves〉上台首演,最後接以〈Thank You〉及部落聚會散場必備的夏國星〈小牧童〉收場。已經跟著音樂跳了 90 分鐘的紐約觀眾,被〈小牧童〉的部落魔性律動弄的意猶未盡,副歌餘波一度延長,人群左搖右晃真成了「臺灣浪」。
和上半場的熱情截然不同,鄭宜農的 set 從今年的新專輯《圓缺》開始唱,凜冽幽暗的台語電氣民謠,主題與呈現方式沉重許多,有關於歷史記憶創痛的〈留佇咱的血內底〉、對抗教條權勢的〈歹物仔〉、頌揚女性成長的〈新世紀的女兒〉。一首首搭配英譯歌詞,帶著觀眾走入紐約的夜,也走入臺灣的暗面。
演唱〈人如何學會語言〉前,鄭宜農用英文介紹台語,介紹歌曲靈感來源與作家吳明益的同名小說故事,一股腦地把對語言的思考與情感交付這首歌呈現。字幕投影一度錯放成下一首〈牽我〉,修正後倒也無傷,紐約觀眾熱情叫喚著,好像也把這份溝通失誤包容、化進歌裡了。
演出尾聲主題逐漸寬大,銜接〈金黃色的〉是加入那屋瓦少女隊後重新編曲、融合排灣語吟唱的〈寬寬仔來到祢的面前〉,以及融合布農族獵物豐收之歌的〈千千萬萬〉。這個版本在 2024 年鄭宜農主持的「邊走邊唱的女子」節目中首度發布,隨後又從台東月光海唱到了紐約中央公園;不只少女隊,布拉瑞揚舞團也上台跟唱,實詞虛字,把寂寞的傷交付集體撫慰。
事後回溯這屆 Taiwanese Waves,發現主演者幾乎都和紐約有著不只一期的交會:
布拉瑞揚舞團藝術總監布拉瑞揚・帕格勒法,曾在上世紀的紐約拼鬥十年,並以「雲門2」編舞家身份在 2012 年的紐約登台;然而這趟卻是他在自立舞團後,第一次帶著布拉瑞揚舞團巡演美國 26 天,途經五座城市、六個藝術節及美術館。
2017 年,鄭宜農曾與紐約待上一個半月,熬過人生最混沌的時期,同年發行睽違六年的個人專輯《PLUTO》與首本散文集《幹上俱樂部:3D妖獸變形實錄》,並在日後漸漸轉入台語創作的世界、自立「邊走邊聽有限公司」成為獨當一面的歌手,再訪紐約演出。
2019 年,阿爆第一次到 Taiwanese Waves 演出時僅發行《Vavayan 女人》,沒想到同年底的《kinakaian 母親的舌頭》在金曲放異彩,續以「那屋瓦」廠牌培育原民唱作新聲。帶著「那屋瓦少女隊」和饒舌歌手 R.fu 重回紐約前,他們已經出演過法國巴黎、非洲史瓦帝尼等國際舞臺。
整理這些過程,我想表達的是臺灣音樂人面對國際舞臺,隱隱之中已經步入下一階段了。踏訪紐約已不求「第一次登上」的宣示,反倒是我們的音樂人在這座城市,已經有成長的故事可以說,包括參與 Taiwanese Waves 工作人員各有各的見證。從第二屆起擔任主持人的台美人 Leo 說:今年觀眾群裡的外國面孔比以前更多了。
當紐約城可以是生活的背景,而非仰慕的遠方,我們方能更自信的表達自身觀點,一如布拉瑞揚老師在《500輯》特刊訪問中說的:「我們不去想作品偉不偉大,而是我踏上舞台,演出,唱了那些歌,我們就代表臺灣、我們就代表原住民——那這件事,就是成功。」
這一屆 Taiwanese Waves 在紐約呈現了什麼樣的臺灣音樂?比起母語創作,我會認爲是更開放的、更有自信的,甚至更團結的。布拉瑞揚舞團會在宜農演出時在側台大聲應援:「太農了!太農了!」演出後還帶著我們幾個白浪圍成一圈,在後台進行祈福儀式、凝聚彼此心。身處異地,更顯特別,臺灣多重語言文化構成的自然語,連同跳舞的身體、相連的手與音樂,或許會是現在的我們能交給這個日趨分裂世界,最不可取代的禮物。
照片提供/Taiwanese Waves;攝影師/Michael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