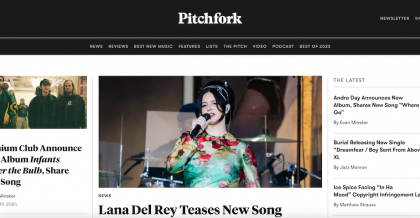舞台上的團員造型野蠻,背景巨幕的圖騰野蠻,和開場的工廠環境音、四處遊走的無塵白衣人形成對比。他們是拓荒的十人,已知用火、手持樂器,在人類文明的垃圾時間裡,伴著德布西的月光登一座山。
從〈Kite War〉到〈Burgundy Red〉,雪花紛飛,細瞧竟是綠色的那應當是葉片了。當白衣人吹掃滿室葉片、往中央堆,葉片落地生根竟成了一片青草地,霎時間,Young Man 告別首爾、Flat Dog 行萬里路,行軍的節奏,讓北流的舞台生機盎然。
知道觀眾想聽金曲串燒,但 hyukoh 與落日飛車的 AAA 巡演遠超於此。這不僅僅是一場「演唱會」,結合劇場形式,AAA 構築在兩團扎實的音樂性上持續實驗跟進化,執行上最精彩的一段,是透過 live cam 的現場影像、預錄影像、現場影像裡的現場影像(比如那台播著〈New Drug〉歌詞的手機),讓虛實不停交媾、生產、再交媾。
國國和吳赫的 vocal 一乾一濕,領著兩團器樂配置也互為表裡。在他們的鏡像裡有彼此,也有搖滾樂史,有友情,也有演奏當下的張力。當〈Hogi Hogi La La Jo〉樂手輪流 solo,兩台攝影遊機各自就位,隨導播來回切換,影像似乎也自帶節奏,強化了節奏。
〈Antenna〉的鬼才 MV 導演 Rafhoo 是這次的視訊執行 VJ。〈Goodbye Seoul〉閃現的飛鳥深影,在〈Pinky Pinky〉的俯角鏡頭中探頭。牠是被翻拍的那支手機裡的傳訊者,墜死地表被團員的 AI 分身發現,最終被葬入〈Antenna〉MV 世界觀裡的沙灘。
魔幻的墜鳥故事所言何事,難以直述。只知此後音樂越發溫柔,〈New born〉、〈Antenna〉緩慢到像是不會結束的飄遊。現場版〈Candlelight〉掃卻疫情間的暗黑 synth,銜接〈Let There Be Light Again〉、〈Vanilla/Villa〉都成了聽覺的庇護所。
墜鳥葬身,圖騰巨幕落地,AAA 舞台元素是兩小時的減法,一層層蛻去後,唯有音樂不滅,緊扣觀眾。
至此我才發覺 AAA 原來不是一場十人成團的登山秀,也是「兄弟下山,一起努力」的患難與共。
hyukoh 成立十年,飛車成立十五年。他們在韓國與台灣,都曾開拓出同輩玩團人所未見的風景,如今成員也已年過三十陸續奔四,體力與意志都在滑行,全球市場卻更競爭了,亞州各地觀眾品味也更刁,當我們著眼《AAA》是 hyukoh 的回歸作,卻常忘了這對飛車而言,更是一座無例可循的巨峰。
集結兩團寫歌、錄製一張專輯、跑一輪亞州巡迴——從去年五月到今天,形似三座小山的 AAA,路途有起有落,上去過的他們總得安全落地,方能再登下一座。
〈TOMBOY〉壓軸後,安可第一首是飛車曾在 2020 年重製過的〈Help〉,此時可以感覺團員的表現都更放鬆。最後的〈2F 年轻人〉,團員手持「台北」與未能到場的鼓手仁雨照片揮舞,國國甚至改詞「推銷周邊」,並「貢獻難聽」模仿 Liam Gallagher 唱〈Wonderwall〉,作為台北的隱藏曲目。
我想接下來的 AAA,可能不會有比這場更好也更特別的 ending 了。在歷經了奇幻的國際級表演後,出現那麼專屬於台灣的內哏,連結台下,9/14 這一夜的與會者,或搖頭晃腦、或高舉手機燈,我們慶祝,慶祝有了飛車的 hyukoh 不會成為墜鳥,有了 hyukoh 的飛車也將如圖騰,終被刻印在搖滾樂的巨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