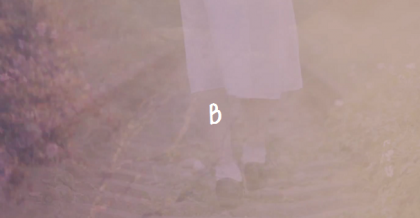如果要構思一個超級英雄的故事,我想寫一個叫做紙巾人的角色,能力是好好地聽每個心靈受傷的人說話,陪著他們將傷口上的污垢和血淚都擦拭乾淨。每個人都需要這樣的英雄。
關於 Super Napkin x 《Rhythmic Lizard Moon》
小帕:吉他/Vocal
黃尾:貝斯/Vocal
施霖:鼓
Q:請用一句話推薦這次的新專輯。
如果你覺得「月球上有隻看著地球哭泣的蜥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這張專輯適合你。
Q:製作這張專輯與錄音過程,期間發生印象深刻的事或有趣的事。
施霖:印象最深刻就是每一次錄鼓的時候(我們在練團室宅錄)都會發現錄出來的品質比上一次更好,所以好想就這樣一直一直錄下去(笑)。
小帕:《Rhythmic Lizard Moon》(節奏的蜥蜴之夜,以下用 RLM 縮寫)整張除了後製送到美國的工作室之外,全是 DIY 製作,用這幾年常見的字眼來說就是「宅錄」。大概從十多年前還是大學生的時候受 Lo-Fi 影響很深,就開始嘗試 DIY 錄音,從什麼都不懂直接吉他一條導線接到電腦音效卡開始摸索。在兩年前我另一個團 Slack Tide 出了錄音室 EP《就這樣別走》後,我一直想要重新挑戰 DIY。除了現實面的考量外,更多是想要回到探索過程,自己去從錯誤和實驗中學東西。
印象深刻的事情大概有三個,第一是所有製作中途覺得太難處理、難到開始自我懷疑歌本身根本沒寫好、準備要拋棄掉的曲目,等到最後熬出成品時都是我們覺得整體感最平衡的曲子,像是〈Solid〉、〈八月二十五〉,感覺像我們在寫歌時不小心遇到了這些歌,等錄音的時候才重新學會要怎麼詮釋這些歌。
第二是原本預想為主打歌,也認為最難處理的〈Brahe〉,結果最早成形。由於錄音過程是多首歌同時在進行,所以一開始的感覺非常迷惘,像是放了九盒模型在面前,可是一張說明書都沒有,連要拼成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所以當某個熬夜混音的晚上東轉轉西湊湊,忽然〈Brahe〉就拼出來的時候,感覺就像「啊,原來是九台噴射機呀!」這樣,開始對整張專輯有比較明確的想像。
第三是發現自己已經到了熬一天夜,就要補三天回來的年紀。
Q:聊聊唱片包裝設計跟音樂的關連。
小帕:專輯封面是好朋友正媛畫的。我過去看到一些她上傳到自己網站的作品,覺得同時很溫暖又強烈,所以印象深刻。去年初樂團正式開始表演的時候,她和宗儒(vuLner、MassMan、C++)有來捧場,因此提到幫我們畫專輯封面的事情,她很有義氣的一口答應下來。我們初期的歌比較 Lo-Fi 一些,所以原本討論出來的構想是一隻捲在衛生紙捲的王者蜥(和我一樣凸眼),手拿著一副眼鏡(眼鏡才是本體),往這種稍微詼諧的路線。不過快一年下來,我們的歌朝著另一個比較內斂的方向前進,而原本的蜥蜴模特兒(正媛朋友的寵物披薩)也離開了人間。一月底的時候我們進行了最後一次討論,正媛沒幾天就把伏在月球上,遠遠地看著各種世間故事掉淚的蜥蜴畫好。和我一開始對她作品的印象一樣,非常溫暖又強烈。
Q:請挑出專輯內的一首歌,送給一個人或一個特定族群。
〈Time to Understand〉,給受到壓迫的人。
Time to understand what’s your name
時候到了,該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麼了
Time to understand where I am
時候到了,該知道自己在哪塊土地上了
Time to make it right with our rights
時候到了,該用我們的權力做對的事情了
Time to make a change with our hands
時候到了,該用我們的雙手改變了
So let us kick some stupid ass(es)
一起踢踢那些渾蛋的屁股吧
So let us kick some stupid ass(es)
一起踢踢那些渾蛋的屁股吧
Q:請說出此這張專輯內「你最喜歡的一首歌」。
施霖:〈Brahe〉。
小帕:〈如果你能接受〉。這首歌的歌詞是對自己還有很多朋友想說的話。從開始寫歌到現在起碼有十年,中文歌詞是我覺得很難跨過的一關,一直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說話方式,能直接唱出想說的話,同時不覺得害羞。在寫 Super Napkin 的歌詞時想克服這個問題,而〈如果你能接受〉算是跨出的第一步。文字本身一點都不華麗,像是在說教一般,不過是一顆我想投的直球。
如果你能接受
如果你能接受,這世界的不完美,就能省下很多淚水
話講得太明白,也許失去了美感,只願你在需要時想起
我也一樣的,他也一樣的,你也一樣的,我們都是這樣的
想通並不難,難的是習慣,習慣把過去當成自己
想證明自己沒有錯,把改變誤認成罪過,我懂
我也一樣的,他也一樣的,你也一樣的,我們都是這樣的
Q:《Rhythmic Lizard Moon》專輯名稱是希望傳達什麼?團名的意義是?
小帕:專輯名稱《Rhythmic Lizard Moon》是對著封面看圖說故事,要傳達的就像上述提到封面時說的一樣。這個詞其實也是馬雅曆法的其中一個月,覺得有節奏、有蜥蜴、有月亮,就借來用了。
團名會取 Super Napkin「超級紙巾」這看起來有點荒謬的名稱,是因為那些就算知道自己的弱點還是要慢慢前進、不起眼卻不低頭的角色對我來說是最有認同感的。如果要構思一個超級英雄的故事,我想寫一個叫做紙巾人的角色,能力是好好地聽每個心靈受傷的人說話,陪著他們將傷口上的污垢和血淚都擦拭乾淨。每個人都需要這樣的英雄,可是在現實中不是每個人都能遇到。我們的樂團介紹有一句「擦你心靈的屁屁」,就是希望做出來的音樂,能讓喜歡的人暫時忘掉一些心裡的重擔。
Q:熬出了一張完整專輯,目前還滿意嗎?是否接近了自己的烏托邦?還有什麼想修正改良的地方嗎?
施霖: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除了 Master 以外,以自己的力量完成了這張專輯,現在回頭來看依然是一張很滿意的作品。我覺得音樂的方向我們已經在這張專輯中找到了一條想走的路,之後就是不斷的磨練音樂性,樂器技巧和演奏默契嘗試將我們的烏托邦更具體化。
小帕:我們三個都是上班族,所以錄製這張專輯的半年來,幾乎是把所有放假時間,跟很大部分睡眠時間都投入其中,沒有什麼放假,累積蠻多壓力和焦慮。因此當收到後製好的成品,終於可以鬆一口氣的時候,回歸日常生活就是烏托邦了。要修正改良的應該是我 mixing 的工作效率。
Q:完成這張專輯最想感謝什麼人(或組織)?他們以什麼方式協助?
施霖:最感謝的是阿呆,願意借我們鼓組的收音 mic 讓整張專輯能以宅錄的形式誕生。因為這組 mic,我們才能在錄音、混音的過程中不斷的發現聲音、演奏技巧、編曲的完整度、樂器間的配合有更多更多的進步空間。真的非常感謝阿呆給我們這個機會嘗試。
小帕:我覺得人沒有什麼是「靠自己」得到的,生命中經歷的所有事物都是他人的賜予,對於玩團這幾年遇到的所有朋友都很感謝,沒有受到大家的影響就不會錄出這張專輯,真的要細數數不完。你們知道你們是誰,請對號入座。
特別感謝團員及團員的親友,投入在專輯的時間其實就是犧牲掉陪伴他們的時間。
Q:創作的主要靈感來自哪裡?可否分享創作的過程?以及如何歌曲和曲序定案的?
小帕:音樂層面主要的靈感還是來自團員彼此,以我們能完成的方式,完成我們自己想聽的聲音。看起來好像是很累贅又理所當然的一句話,不過對我來說,算是一個見山又是山的過程。一開始做音樂的時候,什麼都還不是很懂,所以真的只能手邊有什麼就做什麼;等到稍微深入之後,開始總是看著自己手邊沒有的器材,沒做過的風格;而從 Super Napkin 組團開始又回到了看著團員彼此對音樂最直覺的反應,看看自己手邊有的聲音,想辦法將既有的元素最大化,每一步都攤開來彼此討論。
歌詞方面,好像過了一個年紀後,比較能把事情整理成想法和心得(希望不是思考僵化的開始),大部分都是曾經或想要對家人、朋友、自己說的事物。年紀比較輕的時候會絞盡腦汁去想要呈現怎樣的意象、感覺,現在就是起了頭後面就囉嗦一堆話出來了。
曲序是結合好友/樂評林易澄及 St. Sloth Machine 首腦酪啃的意見編排。以他們的聆聽經驗安排出來的曲序,我覺得是這些歌曲最完美的排列組合。
Q:可否聊聊自己聽的音樂?如何影響到你們這次作品?
施霖:我聽的東西直到加入這個團之前都是一些很主流的 Grunge/Pop Rock,像 Foo Fighters、Muse、The Smashing Pumpkings、東京事變等等,所以編曲時會不自覺的往重和複雜的方向處理,不過後來漸漸由小帕分享的歌單稍微打開了一些對聲音的看法之後,現在會比較傾向於將鼓也作為一個旋律樂器來思考。這張專輯中後期的作品裡有比較多這樣的想法在裡面。
小帕:一開始讓十幾歲的我想開始玩音樂的樂團,大概就是 My Bloody Valentine、The Microphones,Yo La Tengo 及 Pavement,後來當然還有 Dinosaur Jr.、Sonic Youth、Neu!、Bob Mould 等一掛 80’s、90’s 的樂團。不過這幾年影響自己最深的,還是要屬一起玩過音樂的團員(Slack Tide、Sloth Machine、Slow Burning Machine),以及一路上遇到的台灣樂團,雖然彼此不一定熟識,可是無論直接或間接聽到他們創作的過程,或在台下看著他們現場演出及細聽作品,都讓我覺得做音樂的方式千百款,最難也最有趣的就是怎樣找到自身要表達的內容與方式。這些人推動我們的不單是音樂層面,更多是獨立音樂的「獨立」這件事。
Q:對於台灣的音樂生態與音樂祭,有什麼想法嗎?可否分享你們觀察到的音樂現象與音樂環境?
施霖:最有感的觀察應該是 live house 生存的困境吧。心目中理想的環境是大家平常都在各地的 live House 演出,大型音樂祭一年一到兩次。近年大型的音樂祭蓬勃發展雖然讓更多人接觸到獨立音樂,但卻壓縮到 live House 的空間,大家會覺得我花 1000 多塊的門票可以看幾十團,為什麼要平常用 350、400 塊看三四個團。
小帕:傳奇樂團故事中,我最喜歡的一則是 Sex Pistols 於 1976/06/04 在曼徹斯特的一場表演,被英國 Channel 4 選為史上最重要的現場演出之一,當時台下的觀眾有 Buzzcocks、The Smiths、Joy Division、The Fall 等,下一個世代最重要的樂團的成員。(細節可讀《 I Swear I Was There: The Gig That Changed the World》,作者 David Nolan,我自首我還沒看過。)
這幾年有一堆關於台灣音樂「市場」經營的批評、分析、專論文章,憂慮的聲音大於樂觀,但我覺得本質上的東西沒變,喜歡音樂、在音樂裡面找到解放的人,有的開始做音樂,有的開始跑現場,有的開始辦活動。一個世代影響下一個世代。
如果以市場的角度看,經營的成敗難易和產品的好壞沒有絕對的關聯,我想這件事情所有產業都一樣。不過獨立音樂的作品和其他「產品」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一切的源頭是「自己動手做自己喜歡的音樂」,而不是覺得這東西能大賣所以去做。以後者為出發點的「產品」確實會隨著整個唱片工業的衰敗而大受影響(因為做什麼好像都賺不到錢了),可是前者只要自己還做得爽、做得來,基本上是怎樣都能玩出「作品」的。
對於獨立樂團來說,表演、錄音,其實就是把自己親手做的東西丟出去(把自己丟出去),遇到能產生共鳴的人是一個算一個,讓台上台下彼此能經驗那個「被瞭解了」的片刻。真正會對樂團造成嚴重影響的,是因為外力介入所以場域不見了,無法接觸到人了。當場域消失或接觸不到人後,樂團自然就會往各種活動、音樂祭、往網路上跑。
會引起多數人共鳴的音樂怎樣都會賣,只會引起少數人共鳴的音樂則是為了同類少數人而存在,想做音樂的人你打死他叫他安靜,他還是會繼續做。樂團應該就放著任其亂長,留場域讓其發揮,自然會有好東西冒出來,而不是破壞掉原有的場域,另一方面又用補助等其他方式控制市場。文化的本質是投資不來的,外來的金錢注入只是讓原有的營運模式苟延殘喘而不是汰舊換新,該是次文化的,應該就要留給次文化自滅自生。
所以,也許換個角度想,這是更好的年代,因為裡頭沒有大錢可賺,所以沒有愛會玩不下去。這幾年有許多完成度非常高、自我風格也強烈的作品(無論是 DIY 或是進錄音室),而且就我所知,今年還會有更多身邊的樂團會推出專輯,我私底下收到的試聽檔案都非常驚人。喜歡音樂的人也在用各種方式「創造」場景(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場景了),只要外力的干涉降到最低,我覺得都會往該長的方向長。
另一方面我想順帶提的是,我們已經從錄音是「高科技」、正常人負擔不起的 60 年代,走到了自己錄音是低成本、低門檻的現代,組一台電競電腦的價格,可能比弄一套可宅錄的設備還貴。Beatles 時代 Abbey Road 的盤帶機只能錄四軌,如果他們當時有一台 MacBook 我不認為他們會覺得「設備不足無法錄音」。我沒有小看錄音師的經驗與知識、錄音室設備的意思,在可負擔起的狀態下,要追求最好的聲音和細節,進錄音室是品質的保證,也能學到非常多東西,只是對於獨立樂團而言,現在能自行完成的事情比過去任何年代都多、都完整,補助與募款絕對不是必要的,也不是無法推出作品的理由。DIY 不等於比較不好聽、對於聲音不講究,反而是要投入更多的時間跟心血去完成作品,不過相對於煩惱動輒四十萬的錄音預算,不停的找方法生錢,把精力全部花費在與資本和市場的戰鬥,我覺得還是運用僅有的資源把事情做到盡可能好比較好玩,畢竟這是自己想做的事情。當樂團口中的話題從怎樣申請、怎樣籌錢,轉成怎樣宅錄時,我覺得錄音的資訊量跟上手度都會比現在好很多。
Q:對於音樂「在地化」與「國際化」,有什麼看法?自己的音樂對於土地或社會環境有連結嗎?
施霖:寫歌的時候不會特別考慮到在地化或是國際化,我認為藝術類型的作品本身就能反映出創作者的精神,我們在這塊土地上長大,聽著中西傳統現代各式各樣的音樂,接觸每一個獨一無二的朋友,這些經歷都會在寫歌時自然的展現出來。我覺得這是我們真實表現生活在台灣的方式。
小帕:台灣是一個長期被殖民、受到各種政權與文化影響、需要「挖掘」身分認同的國家,因此這個問題本身就十分的台灣。我覺得音樂(或各種創作形式)最核心的部分還是誠實,只有把自己最想要表達的東西竭力呈現出來,無論是否與當代價值觀衝突,才有可能成為有力道的作品,讓聽者(創作者本身也是聽者)去思考作品帶來衝擊的部分(與自己不同、沒有經歷過的感受),以及能找到認同感的部分(與自己相似、有所連結的情緒)。所以音樂的「在地化」或「國際化」對我來說是創作者本身是否有這個明確的訴求目標,並成功的表現出來,而這個訴求在台灣是會被放大檢視的。
回到先前講的部分,在藝術的層次上我覺得創作者能成功地傳達自己的概念,就是好的作品,而作品背後連結到的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社會意義都不能只從音樂來討論,那些都是重要的事務,可是不單只在音樂的範疇中,其涵蓋範圍廣於(非大於)音樂作品;同理「在地化」與「國際化」只是眾多創作出發點的其中兩項,並不是對立的。好的作品無論「在地化」或「國際化」,甚至「兩者皆有或皆無」都還是好的。
除了「我們就是在台灣長大的人,做出了這樣的音樂」外,我想不到更能表達這個連結的方式。
Q:接下來的表演活動行程?下一波計畫與最想做的事情?
6/25(六)Breed Records 繁殖周年慶 @高雄百樂門
7/13(三)AutoFocus 自動對焦 @台北 Revolver
7/15~7/17 Wake Up 音樂季 @嘉義文化創意園區
施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製作出下一張比現在更好的專輯!
小帕:大家一起錄第二張專輯。
Q:有沒有話想對團員說?
黃尾:你們是我的最佳夥伴,Super Napkin 成團到發片帶給我很多成長。
施霖:小帕我愛你。
小帕:我換 pick 了。
【快問快答】
Q:你在音樂中得到了什麼,讓你願意堅持下去?
施霖:爽。
小帕:財富與容貌。
黃尾:生活中參與的事太少,藉由音樂學習到跟朋友傳達自己想法的可能性。與團員共事的凝聚力與對共同目標的追求,這些漸漸的都不可或缺。
Q:如果可以跟一個音樂人交換生活一天,那個人會是誰?
小帕:小賈斯汀。他算音樂人對吧?
Q:對你來說,音樂在心中佔了何種地位?
小帕:逃避現實生活最理直氣壯的藉口。
黃尾:小帕常說,如果世界只剩下一座島嶼什麼都不剩的話,我還能做音樂。
Q:你如何分配時間在音樂與生活上?
小帕:在我分配完上班族、兒子及男朋友三種身分後,剩餘的時間都在轉效果器。
黃尾:團員都有正職工作,我目前玩了兩個團(另外一個團 St. Sloth Machine,小帕也在裡面,他還有另一個團 Slack Tide),所以音樂幾乎佔掉大部份可用時間。
Q:可否說說你平常蒐集音樂資料的方式,與聆聽音樂的方式?
小帕:新的音樂大多來自朋友推薦,或是上班聽 YouTube 一些頻道及串流推薦的作品。碰到有興趣的就會去找訪問來看,過程中會碰到其他有興趣的東西。
黃尾:Apple Music、Spotify……等音樂串流或唱片行。
Q:可以分享你個人和音樂人朋友們近期常常談論的話題?
小帕:草東、NBA、入不敷出。
黃尾:Radiohead 新專輯、腳底按摩。
Q:最希望這張專輯被什麼人聽到?
小帕:陳家偉。
Q:如果可以,最想要找哪些音樂人合作演出或錄專輯?
小帕:Kevin Shields 幫我刷節奏吉他。
Q:如果私心想推薦一張專輯,會推薦哪一張?原因是?
小帕:The Microphones – The Glow Pt. 2,我自己人格養成階段很重要、很喜歡的一張專輯。
Q:近期想推薦哪個廠牌或音樂人、樂團,原因是?
小帕:微酸的偷窺狂。近期因為微酸的吉他手踢踢準備當爸爸,代打了一場表演,搶先聽過新專輯的曲目,非常洗腦,洗好後只要一想到旋律就會全身充滿幹勁,適合任何需要動力的人。
Q:最近最喜歡的一句話或一個想法是?
施霖:排球是向上看的運動。
Q:有沒有什麼人物或作品是特別影響你們的?他們以什麼方式影響你?
施霖:最近特別喜歡邁可‧桑德爾,他的所有中文譯本作品都很愛。
Q:最近有什麼有趣的活動是你們想參與的?
施霖:Fuji Rock。
黃尾:
Doodle Endless Dreamless Tour
♡♡♡真珠子個展「通過吧通過吧~我的通過儀式~」5/28 ~6/28 ♡♡♡
Sun Eat Moon Grave Party – Forests(SG) Live in Taiwan 2016
Q:除了音樂,你們平常喜歡做什麼呢?
施霖 & 小帕:看漫畫。
Q:目前最想學習的新事物是什麼?理由是?
施霖:想把日文學好,理由在上一題。
黃尾:日語,太喜歡去日本玩,另外一點是希望有與日團交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