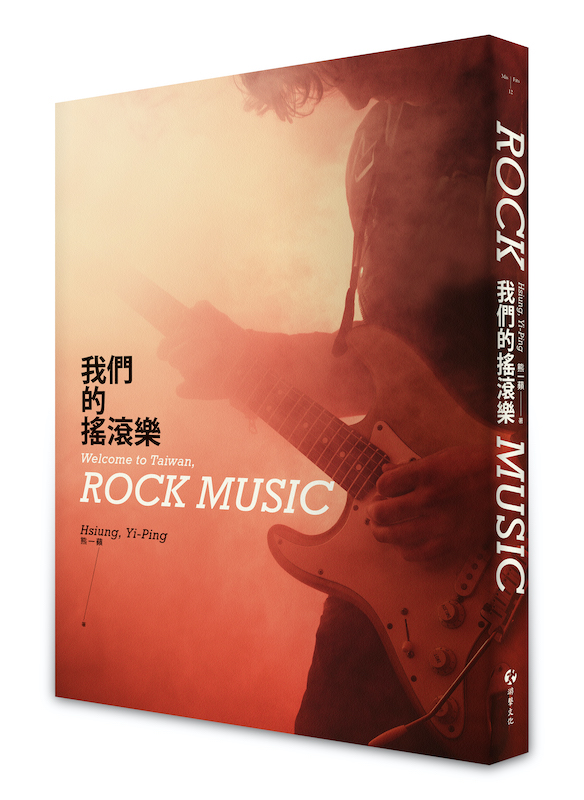文:陳涵(DJ/樂評)
一、世代
在過往有關臺灣流行音樂史的論述,各種出版品中,人們不容易看到從日治時代結束後直至民歌時代這段時間內的紀錄。我們有日治時代臺灣歌謠紀錄片如《跳舞時代》(公共電視,2003)、石計生的《時代盛行曲——紀露霞與台灣歌謠年代》(唐山,2014),也有如張釗維的《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時報,1994);或馬世芳、陶曉清等人不遺餘力的民歌論述。但對於 1950 年以降,冷戰格局下受到美國文化影響的「熱門音樂」,直到 1970、80 年代反映臺灣外交困境,相對於官方「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由廣義的搖滾樂迷所發起的「民歌運動」,在這之間的搖滾音樂如何發展、延續,卻遲遲未見完整的論述。
在 1950 年到 1980 年之間,臺灣音樂發生過什麼事?印象中,在 2015 年出版的《造音翻土》之後,沒有再看過對臺灣流行音樂或臺灣搖滾音樂史更進一步的討論。因此,本書最大的貢獻便是彌補過往缺乏從熱門音樂到民歌運動,針對大眾書寫的臺灣搖滾音樂史。

作者熊一蘋指出,這是在當代臺灣對搖滾樂的「反抗、叛逆或憤怒」有感之前,逐漸「集結」的階段。如果貼著書中研究的主題,也就是搖滾樂如何在 1950-80 的這三十年間,逐漸形成一個或數個世代的集體意識、逐漸成為臺灣的「年輕世代的聲音」。
二、權威,威權
熊一蘋將匯聚起世代的核心動力指向「自由」。以「自由」之名,意味著從某些束縛之中「解放」。因此,本書的主角,1950-80 之間的臺灣青少年,肯定有其欲掙脫之對象。臺灣青少年所欲掙脫的束縛、對抗的對象,某種程度也反過來區分出了和「他們」作對的「我們」是誰。本書名為《我們的搖滾樂》,首先浮現讀者眼前的問題,便是「我們」是誰?
我們是誰?身為「臺灣人」的大哉問。臺灣各類文化深受政治影響,這問題無可避免。本書的「我們」在對抗的是什麼?這個「我們」如何從壓迫之中集結,破繭而出?
在戒嚴、威權政治的年代,誰有本事標新立異?
答案是外省青少年:「陌生的土地、沉悶的生活,外省青年需要幻想來忘掉現實,來自輝煌美國的搖滾樂是最好的材料。」作者指出,對於本省青少年而言搖滾樂不在官方許可的範圍內,因為政治因素而被自然排除於選項之外。但搖滾樂能在高壓控制文化的臺灣生根,卻也同樣來自於政治的腐敗:「在家庭會議中,即使是高中生也能成功拉攏軍政要人,有了重要人士起頭,這一次的特例可能就此變成社會上的通例。」因此,更嚴格地說,有能力跟條件接收搖滾樂的族群,是有特權的外省青少年:「少數青少年利用特權打開的後門,引來的更多的青年,終於影響了整個臺灣。搖滾樂的確是屬於年輕人的音樂。」
搖滾樂在同步引進臺灣的初期,等於是種「家庭革命」,只是,對外省特權階級來說的家庭革命,換作是本省人,恐怕便有遭解讀為「政治革命」的危險。對外省青少年來說是「家長的權威」;對本省青少年而言,則是「國家的威權」。這樣的狀態,持續到了 1970 年代:「世代之間的觀念差異已經大到難以忽視的程度,以外交的危機和官方的壓制為引爆點,1970 年代的臺灣年輕人終於趕上了席捲世界的學潮,開始產生世代意識和認同;這樣的現象,即使在民歌以外的圈子也能看到。」
我們是誰?先是「少數青少年」對抗家庭權威,後是「臺灣年輕世代」對抗政治威權。
三、搖滾在臺灣
某種「年輕世代」的意識形成——從1950年代擁有特權的少數青少年,到1970年代的臺灣年輕人——正與搖滾樂被引入媒體的時間重疊。
不過,搖滾樂是什麼?
作者熊一蘋說:「我要談論的不是一種音樂類型,而是一種與音樂結合的精神,是臺灣青年的啟蒙與行動,是一種持續至今的文化運動……。」
《我們的搖滾樂》一書中,搖滾樂在臺灣的發展大致可區分兩個時期:熱門音樂與民歌。第一個時期,亞瑟(劉恕)1950 年起在《聯合報》的〈爵士俱樂部〉中引介美國排行榜歌曲,隨後他於正聲電台的「我的唱片」節目中將貓王等人的音樂稱之為「搖與滾」。緊隨著亞瑟,曾在《皇冠》雜誌撰寫〈皇冠歌選〉專欄的費禮(平鑫濤)在他的空軍電台「熱門音樂」節目(1957 年起)為這些音樂定了調。
家長對屬於「不良少年」的熱門音樂的疑慮,不敵有心利用熱門音樂的黨國權威。作者帶領我們見證 1950 年代形象不佳的熱門音樂是如何被軍警單位所用,以收買人心(針對的當然是年輕人):「……熱門音樂有號召年輕人的功能,這才是最重要的。」加上「翻版」唱片的生意導向,熱門音樂雖包含許多排行榜的流行搖滾樂,但卻沒能突破流行音樂,形成文化:「……我們的確趕上了與美國的流行時差,但只趕上了主流品味。」
而在年代交界的 1970 年「野人咖啡事件」後,反文化青年們開始不滿於主流文化的沉悶,加以「熱門音樂演唱會」的票價偏高與名單詐欺(該演出的沒登場),「熱門音樂」幾乎消失。與此同時,也開始了新一代的搖滾樂論述。
余光中「質樸的搖滾樂」;張照堂「搖滾精神論」奠定了搖滾樂朝向民謠歌曲的方向,而洪小喬於中視開設的「金曲獎」,則提出了「唱出自己的曲調……」的說法,拓展了大眾對流行音樂的想像力。
與洪小喬、余光中、張照堂等「文青」相對,有李雙澤、胡德夫、楊弦、陶曉清等民歌運動先行者。在引爆「唱自己的歌」論戰的「1976 年淡江事件」中,後者更是可以再區分為「擁抱臺灣與中華」(陶曉清、楊弦)和「排斥外來文化」(李雙澤、胡德夫)的一體兩面,前者的《中國現代民歌集》與後來新格唱片的《金韻獎》系列比賽與合輯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後者,加上後來繼承李雙澤與淡江左翼社群路線的楊祖珺,卻在歌曲審查制度下遭遇作品無法出版的困境。
檯面上,是廣播、電視頻道上主流歌星的「快歌」和「校園歌曲」;檯面下,俱樂部、舞廳、夜總會……等非主流的地下場所,則有「歪歌」和「民歌」。起自 1973 年的審查制度扼殺了民歌的更多可能,但「搖滾樂」的概念卻在民歌運動後進入華語流行音樂。1980 年後,陽光合唱團的吳盛智、洛克斯的羅大佑,以及丘丘的邱晨,特別是後兩者在流行樂壇的成功,改變了華語流行音樂的體質。至此,熊一蘋在故事的尾聲指出:「搖滾樂在臺灣」的時代在此告終,「臺灣搖滾樂」才正要開始。
四、我們的搖滾樂,我們—搖滾樂
在《我們的搖滾樂》裡,「我們」與「搖滾樂」是分不開的。
搖滾樂作為熱門音樂,首先是少數外省青少年用以對抗家父長權威、逃離島嶼生活沉悶日常的寄託;當熱門音樂變成流行(翻版)商品、官辦演唱會,一群「文青」重新定義了搖滾樂,讓它指向民謠;民歌運動或許曾被威權政治收編、阻礙、壓抑,但左翼運動的影響,〈美麗島〉、〈少年中國〉……等歌曲,都透過對於權威的呼應,重塑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定義了當時的「我們」。
自太陽花學運後,近幾年政治領域中,討論「世代」的論述又多了起來,《我們的搖滾樂》在此時此刻的臺灣出現,也未必是種意外。想起有回與 Waiting Room 的「師大公園地下司令」Ahblue 聊到,覺得 318 那時,大家似乎有著共同對抗的目標,使不同風格的獨立樂團與群眾聚集在一起,也成就更多的改變與力量。從當下這個「獨立樂團」百家爭鳴的時代往回看,或許正是當搖滾樂開始更積極參與社會改革,「搖滾樂在臺灣」才真正地成為「臺灣搖滾樂」。
我們的搖滾樂……我們就是搖滾樂,唯有內化它的精神,才能唱自己的歌。
換言之,我們才真正地成為「我們(這個世代)」。
(本文由《我們的搖滾樂》書評作者及游擊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登,未經同意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