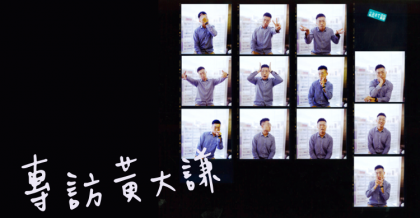即將在 3 月 29、30 日登場的第 16 屆大港開唱,先前公開特別企劃「再會陳一郎:相逢大港邊」。
由閃靈樂團主唱 Freddy 擔任節目監製、金獎製作人柯智豪則是音樂總監,邀請黑狼黃大旺、金曲新人洪佩瑜、樂團 A_Root 同根生登台獻唱,另外還加入知名薩克斯風手謝明諺,結合三立電視台授權之陳一郎演出影像片段,透過 AI 數位科技技術,重現「酒國歌王」陳一郎傳奇風華。
演出前夕,我們跟 Freddy、柯智豪相約在出日音樂辦公室,從接觸陳一郎的過程開始聊起,再到他的歌聲特色、節目製作上的挑戰,與那殊途同歸的台語歌傳統,如何形造成超越時代的影響。
「這並不是陳一郎紀念演唱會。」Freddy 強調要有一種新鮮感才趣味,大港開唱本來就會找資深的歌星合作,從之前的賀一航、沈文程到陳雷、黃西田,「只是這次是請到陳一郎,然後我們想辦法讓他活起來。」
時光回到 1953 年,陳一郎生於屏東,本名陳銘農,天生擁有一副好歌喉。原以修車為業,某天意外地被伯樂挖掘,簽約唱片公司發行〈阿郎阿郎〉、〈行船人的純情曲〉等代表作,奠定他在八〇年代台語歌壇一哥的地位。另一方面,由於歌詞經常出現「浪子」或是「港邊」的離鄉心境,他更成為藍領階級的代言人,只可惜生平愛酒,年僅 47 歲就因為肝癌離世。
為了這次合作案,音樂總監柯智豪回頭聽陳一郎,小時候的回憶全然湧現。「當你在找自己的時候,會開始瞭解我是誰?我要去哪?這些音樂就會浮現,告訴你其實你是這樣長大的。」他認為集體記憶在分眾時代越來越可貴:「有時候寫歌會覺得很奇怪,怎麼會開口就是這種東西,完全刻在血液裡面。」
不論是閃靈、拍謝少年、茄子蛋還是百合花,Freddy 認為這些聽團仔會聽的台語歌,裡面的飄撇或是苦情,源頭就是陳一郎那一輩台語歌手,只要用台語創作就很容易顯現的一種心情,其實是超越時代的。
「我覺得他太早走,也不是在人生比較旺盛的時候離開,不像高凌風還有那麼盛大的回顧。」Freddy 感嘆這位歌聲曾響遍加工廠、漁港的「酒國歌王」,逐漸被社會遺忘了,因此藉由這次節目,他希望:「讓他的家人知道,就算他沒有很風光的離開,但他的音樂、歌聲其實都留在台灣現在的音樂裡。」
與一郎第一次接觸
Freddy:應該差不多國小一、二年級,親戚長輩們都會放陳一郎的歌。
柯智豪:我們兩個同梯(年)的。陳一郎真的是生活中會很密集看到的明星,一路紅到我們國中的時候,後來電視節目開始比較蓬勃,他也會去上綜藝節目。
Freddy:對對對!開始會有「瑪爾寇陳」的腳色。(編按:九〇年代初,陳一郎曾以英文老師「瑪爾寇陳」的角色,在綜藝節目中以台語口音的英文與主持人互動而走紅。)
我覺得陳一郎的定位還是很有特色,歌曲比較「飄撇」一些,面向海港、討海人,跟葉啟田的風格不太一樣。他的唱腔也很獨一無二,顆粒比較粗,也不確定那算不算是酒嗓?
柯智豪:如果用南管的講法,陳一郎算是把字頭、字身、字尾處理得很清楚。現在大家很少處理這個,講話也都很黏。他和其他歌手講述的故事也稍稍不同,陳一郎比較基層,講兄弟情、喝酒、談戀愛,或是我怎麼這麼悲哀、怎麼沒有成功這類的。
Freddy:那時候替他寫歌的人,也是有 A&R 的。
柯智豪:他的唱片就是跟討海人愛用的「治痛單」綁在一起的。
殊途同歸的「台」味
Freddy:其實要發現這些本土歌星對自己的影響,大概都已經是開始創作以後的事了。尤其是千禧年之後、YouTube 開始普及,所有台語老歌、歌仔戲都開始有人上傳,我才發現,「啊怎麼每一首我都聽過、都會唱。」
柯智豪:那個察覺很特別,有時候寫歌會覺得很奇怪,怎麼會開口就是這種東西,完全刻在血液裡面。
Freddy:對對對!創作的第一階段幾乎都是模仿,不管我喜歡的 A 團、B 團、C 團,就先模仿看看;再來不想一直抄襲別人,要回來找自己的時候,就會發現怎麼想出來的旋律都土土的、台台的?才知道有一塊東西一直放在那邊。以前覺得它不存在,但音樂一放下去,你才終於懂寫歌的時候那些「台味」是從哪來的。
柯智豪:我最有印象的是〈紅燈碼頭〉,另一首〈可愛的馬〉其實不是他的歌,但他的專輯有重新再唱一次。
我本來不知道 Freddy 也是這一路的,沒想到他也是聽這個長大的!以前真的會有一種美好,是大家都在看一樣的東西,那是很深的記憶。有共同的記憶去形塑一代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這件事在現代越來越難,因為太分眾了。
Freddy:我覺得尤其在台灣,其實分眾以後大家還是可以在龐克、金屬、民謠⋯⋯各種不同風格裡面發現一些「台台的東西」,那就是小豪老師講的那個共感,分眾的源頭。
柯智豪:也許還是有個最核心的東西可以被感受,有一個骨子裡的東西是一樣的。
「酒國歌王」不該忘
Freddy:我對陳一郎最有印象的歌是〈行船人的純情曲〉、〈再會!乾一杯〉。雖然那個時代的歌手,可能多少都會有一些跟碼頭、港邊有關的歌,但陳一郎大概是唱最多的,不管是在加工廠、還是出海捕魚,只要跟海有關的都是他的 TA。
最早以前講到陳一郎應該是差不多十年前、2015 大港開唱復辦的時候。我就一直說,要不要有一個舞台就用觀落陰的,我們直接精選十首、把陳一郎的影片從頭播到尾。
柯智豪:大家紅布條戴上去,現在可以請裝咖人上台。
Freddy:對對對!就感覺他在現場唱,結果一講就被大家罵,說我在亂弄。我現在已經退出大港開唱團隊,但是去年立委卸任以後,又來參加他們的會議、在旁邊打雜,就發現 AI 好像有搞頭。
柯智豪:那時候有別的名單嗎?
Freddy:我沒有特別去想,就只是在旁邊戳一下、戳一下,沒想到這次他們也覺得好像可以。剛好小豪那時候也在國宴上做了文夏的 AI 重現,大家一拍即合就開始做。
陳一郎有點慢慢被社會遺忘了,所以好不容易有這個特別企劃之後,我們也希望可以聯繫到他的家人。一開始著手聯絡他的朋友,包括以前廣播界的長輩,連歌壇的大大余天我也去打招呼了,大家都去幫忙找,最後還是聯絡不太到。
一直到我們的活動發布後,陳一郎家屬的友人主動寫信聯絡主辦單位,表示家屬很感謝特別設計這一檔節目。我們有邀請家屬一起到場觀賞,但因為長輩年事已高,所以不方便到現場觀賞,不過我們會錄製影音給他們留念。我們希望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陳一郎雖然離開的很早,但他的音樂、歌聲其實都留在台灣現在的音樂裡。
人人都是陳一郎
柯智豪:這次引用了 deepfake 的技術。最困難的是,以前那些素材的解析度最好也只有 480P,他又走得早,根本沒有任何更清晰的影像,很難訓練 AI 模型。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先製造了十幾萬個人工做的陳一郎,再把它餵給 AI,這樣反覆訓練了大概一個月。
我們都知道陳一郎有顆痣,在訓練過程中,如果臉轉向不同角度,那個痣有時候會突然不見,或是因為我們的素材裡很多是陳一郎拿著麥克風,所以那顆痣有時候會突然變成麥克風。
現在比較要克服的其實是「即時性」這件事情,因為是現場演出,所以那個速度感會相對重要。比如說鏡頭往台下一拍,所有人的臉都要變成陳一郎,那運算速度要很快,如果可以掌握秒差,我相信可以用很多表演的設計讓這個東西變得很有趣。我們剛剛跟 NVIDIA 調了最大張的卡,技術團隊也還在想辦法突破。
這之前在國宴上做文夏老師的 AI 重現,兩個是不一樣的技術。那個影片很真實、唱出來也是文夏的聲音,真的一模一樣。可是那時候我突然覺得,這跟看影片有什麼兩樣?好像差了一點魔幻感,我覺得魔幻感其實不是要把東西做到最真,而是你怎麼讓真跟假是錯亂的。
這次演出者在台上,你看到的是大旺、洪佩瑜、同根生本人,可是視訊轉播出來的是陳一郎,他們之間又可以連動,甚至只要鏡頭拍到的都會變成陳一郎。這會把虛跟實破解掉,所以也不用追求到最真。對現在的人來說,最真實就像是看影片,有點不好玩。
「這並不是一場紀念演唱會。」
Freddy:你可以想像,大港開唱本來就會有很多資深的歌星來合作,只是這次是請到陳一郎,然後我們想辦法讓他活起來。
柯智豪:就是穢土轉生啦!
Freddy:我們都 50 歲了,都是健康有問題的人了。其實現在做很多事情,除了自己爽之外,大港開唱裡面這麼多聽團仔,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喜歡的這些音樂是從哪裡來的?未來會變成什麼?是我們這一代的人差不多要做的事情。
從之前的賀一航、沈文程,到後來有陳雷、黃西田,他們來也不是完全唱以前的歌,要怎麼跟現在的樂團合作,同時保持他本來的風格,有一種新的感覺,這才趣味。
柯智豪:Freddy 講的很重要,如果這些長輩或是資深的音樂人來到大港開唱,還是用以前的樣子呈現,那我們就沒有辦法把這些記憶交給下一代。我就要用下一代覺得「看起來好爽」,看完這輩子忘不掉的方式去溝通,才能把這東西傳遞給年輕人。
所謂的音樂感官、現場的這些事,是可以被設計的,而且我們知道那個方法是什麼。用這個方式把我們要傳遞的陳一郎放進去。可能看完這個表演,你記得的是台上的人變得很奇怪;或者是你覺得,這歌聽起來這歌好爽,這就是在拼湊整個體驗的過程,有了體驗之後,也許有幾個人就會覺得好奇,去查資料,或是來和我們聊聊天。
找自己也是找彼此
Freddy:我覺得可以從一個角度去想,不管說現在聽的台語的歌曲是閃靈、拍謝少年、百合花、茄子蛋、同根生。這些台語歌有的時候都有一種飄撇或是苦情,華語的歌怎麼好像都沒有這種浪子的東西?但是當我們唱台語的時後,即便是現在的曲,它都有一個奇特的悲傷感,那是從哪裡來的?我覺得就是從陳一郎那一代來的。
其實台語歌就是從日治時代、一路進入工業社會以後,台灣社會在這個巨大的變動裡面的各種不適應,這些基層的人想要唱的歌。最後由這樣的語言、文化、音樂,唱出來的一種感受。
柯智豪:我也想要呼應一下 Freddy 說的。他說的也跟剛剛提到「共感」很像,可是這個苦情到底要不要傳遞、蔓延到下一代去,我其實也有問號。畢竟年輕的一代不像我們是從戒嚴時代過來的,感受過很多悲情的台語歌。
可是我希望透過這種形式,記憶可以互相交流,一旦交流才會知道我們是生活在一起的,那個交流的點就會變成跨越年紀的共感。有時候找自己也是一種找彼此,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一旦沒有這件事,音樂、文化的交流都會失去意義。
Freddy:從 2006 年開始辦大港開唱,就很強調創作、很強調在地,甚至是希望可以有更多南方的樂團。我覺得這些成長只是回歸一個自然。(編按:指大港開唱開始完售這事情。)
因為我們剛開始去 Fuji Rock 的時候,看的團包括日本團也是外國團,對於音樂祭都是很國際型的想像,不會是以本土為主。加上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外國團來台灣的票房都不錯,TICC 也能賣完。現在本土團在北流也可以賣光,國內團聽的人會比外國團多,回歸一個正常,代表獨立音樂與本土文化成熟的一個象徵。所有的音樂本來就從這塊土地的故事開始。
現在的聽團仔,聽到拍謝少年、百合花的歌,可能會覺得那個苦澀只是來自他的生活。但如果我們往前把陳一郎拉出來,就會發現這其實是超越世代的,只要用台語創作就很容易顯現的一種心情。
或許你會發現,你跟爸爸一樣喜歡某一種歌曲,只是他喜歡陳一郎、你喜歡新的樂團,這背後有一個類似的東西,這個時候,你活在這個土地的深度就出來了。
採訪、編輯/王信權
文字整理/温伯學
攝影/蔡耀徵